
時代瘋魔,文本成活——陳雪《親愛的共犯》影集版確定!
+ More 有沒有這個可能:你抓到了犯人,卻不希望是他們?山上一間純白的高級住宅,山下一間不見天日的育幼院,解謎如解夢的警探,犯案如自白的共犯,案件涉及十幾年,十七人全員嫌疑,被害者不一定乾淨,但加害者一定有問題⋯⋯?為了愛,我們下地獄,一層、一層、再一層地走下去。———————————————————「我一直想寫暴行,施加於人卻無形的暴力,例如控制與剝奪。」——陳雪———————————————————現代社會派推理最高傑作!第十五屆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陳雪《親愛的共犯》(鏡文學出版),日前售出影視版權後,正全力進行影集版的大型影視化工程,而純文學出發,行經了同志文學、愛情散文和人妻日記,一路走到了犯罪小說的惡女陳雪,作品多次獲文學獎,影視化歷史更是閃閃發光。———————————————————《蝴蝶》(印刻出版)改編之香港電影《蝴蝶》,獲台灣金馬獎最佳新演員獎、最佳改編劇本獎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獎,香港電影金紫荊獎最佳女主角獎、最佳男配角提名、最佳女配角提名,巴黎女同志和女權主義者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另選為香港同志影展開幕片、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國際影評人週閉幕片。「★★★★★★★★★(9/10)」——《IMDB》、「非常好的角色研究。」——英國《螢幕週刊》。———————————————————《摩天大樓》(麥田出版)改編之中國騰訊影集《摩天大樓》,獲豆瓣8.2高分,中國初心榜年度五大青年導演提名、年度傑出平台型製片人提名,中國華鼎獎年度電視劇滿意度調查百強第13名,中國指尖傳播影響力報告年度最具影響力短劇集獎,中國金骨朵網路影視線上盛典年度品質短劇集獎,章子怡、郭富城、林心如、徐崢——發文推薦。「★★★★(4/5)」——《豆瓣評分》、「敘述手法獨特清晰。」——章子怡(演員、電影製片人、導演)。———————————————————時代瘋魔,文本成活,陳雪第③部影視化作品——跌入人間荒涼、焚燒人心火花、思辨人類罪罰之《親愛的共犯》,影集版全速開發中,我們一步、一步、再一步地走下去。

陳雪七宗罪 ——陳栢青讀《你不能再死一次》
+ More 《摩天大樓》後,陳雪開始一個人的攻頂。「二○一五年出版《摩天大樓》之後,感覺自己好像走到了一個陌生而孤獨的地方。」之於這位文學中的惡女,社群媒體上讀者信賴的愛情導師而言,接下來的路,像一個人爬一○一,三年三本長篇,綁架,殺人,謀殺,懸疑推理,那是往上飛昇還是朝下跌落,他把臉書當樹洞一樣寫:「我在黑暗中摸索著,我知道我在做什麼,可是很難對他人說明,我感覺自己逐漸遠離熟悉的路,我甚至擔心自己的轉變會讓我的朋友們感到不解或失望。到了五十歲才放棄熟悉且擅長的,我面對的是無止盡的挫折,有時我會懷疑自己,這樣走下去,會不會兩頭空,會不會後悔,我是不是走錯了路,我為什麼非得挑戰不可能?很多疑問會在睡前浮現,令我輾轉難眠。」另一篇:「有生以來,我第一次對自己的寫作能力感到懷疑,我也懷疑自己所為何來,我很早就成名,有滿滿的作品在身,一個五十歲的人,在這時要轉變路線,書寫自己不熟悉不擅長的題材與類型,這時重頭學起,是為了什麼?」殺人不能回頭。寫作也是。二○二二年,《你不能再死一次》出版了。小說中鎮子似若存在詛咒,間隔十數年,美少女透明若無物的身體橫陳大樹下,增加的死亡人數疊加成虐殺三聯圖。這一回,謀殺地圖幅員更大。手法更殘。死者人數更多。已經回不去了。不做好女孩,就成了惡女。不作以前大家熟悉那個純文學作家,那陳雪會不會成為罪人?固然「你不能再死一次」,但陳雪可以在寫作生涯裡壞上幾回?《你不能再死一次》陳雪著出版日期:2022/6/10一、看陳雪作了什麼,不如看陳雪不作什麼。陳雪當然犯了罪。他最大的罪,不是背離所謂的純文學──「逐漸遠離熟悉的路」、「甚至擔心自己的轉變會讓我的朋友們感到不解或失望」──但我以為他真正的罪在於,他並非踏上通俗之路,他跨界,但殺的不只是純文學,在《你不能再死一次》中,他也同時把刀伸向類型。終究,「展示,不要講述」成了現代所有寫作教科書的共同信條,SHOW,DON’TTELL。豈止純文學,我以為這句話更是成為驅動整個通俗文類的火車頭,讓單純的敘述句鋪開來成一段又一段的情節和畫面像火車車廂轟隆朝讀者駛來。《你不能再死一次》卻在這裡大刀闊斧和類型走向相反之處。試摘《你不能再死一次》段落:鐵雄跟宋東年讓陳茶跟萬老大等人都先回去候傳,勒令他們暫時不許離開桃花鎮。鐵雄把皮夾交給鑑識組,就和宋東年直接去文化路找宋老闆要相機,董老闆把相機交給他,可惜檢查之後發現裡面沒有照片。六句話,六個標點。放在別的小說裡,從鐵雄、宋東年、陳茶、萬老大乃至董老闆表現各自人物描寫和性格,過場來往互動試探交心對手戲全交代,沒五千字跑不掉。陳雪三行就完事了。乾淨俐落。這樣的簡潔線條構成《你不能再死一次》中大部分辦案的篇幅。陳雪不作,他不作通盤的「展示」,他反過來「講述」,案件流程與次要人物的來往被大幅度縮減,小說被陳雪壓的很緊,很實。細究之,通俗文本需要的「展示」意味的是什麼?照字面所示,方向上是影像的(讀者看小說彷彿看實境秀、新聞、YouTube影片、關鍵時刻、刑案實錄),他讓你感覺到真實,敘述者隱退了,什麼都由某個角色代言,那產生一種擬真的幻覺。而在實質意義上,不如說,「展示」事關資訊。通俗文本的進化在於,如何包裝資訊。不只是要讓讀者接收情節推動的必要資訊,更讓這份接收變得富於樂趣。所以展示所謂「SHOW」是否具有另一個雙關:通俗文本,無論戲劇或是小說,此刻變成一個秀。如今,一個成熟的通俗文本不會只是寫「女孩死去了,屍體被發現了」,他更可能寫的是,「X年Y月Z號下午,OOO發現了屍體。這將永遠改變OOO的人生。」書寫者更傾向於推出一個角色,給了他名字OOO,長出臉,甚至有了背景和家庭,精熟於此道者還要賦予OOO人生背景。葉子藏在樹林裡。資訊藏在膨脹的橋段中。故事長出更多故事來。無可厚非的,通俗文本越來越無非可厚的了。此刻的類型縱然被粗分為犯罪/推理/懸疑/神祕/科幻,但其實開展出的情節包羅萬象,因為與其說它是類型,不如說,類型成了載體,讀者不只是要接收到作者預設的必要資訊,這必要資訊可以延伸為極短篇。單獨摘出,都有閱讀的樂趣。陳雪能做得到嗎?事實是他做得很好。前作《親愛的共犯》寫豪門謀殺案,貴冑大戶隱於深巷內,卻成為小說裡所有角色目光焦點,打掃阿婆、鄰居歐巴桑,大家都在抬頭望,一個人一種敘述,多一道聲音就多帶出一條線索,小說家是老狐狸,《親愛的共犯》中不只把豪門和上流世界看得通透,也昭示他對通俗小說結構和技術知根知底。要我說,那就是陳雪完全知道通俗小說的操作,知道怎樣用小說的公設騙地板面積,你花了錢,未必用得到,或只能用一次,但能看到也是爽。但在《你不能再死一次》裡,小說家住回去老公寓了。實打實。非常省。一坪是一坪。那使得《你不能再死一次》和坊間類型或說一般通俗文類切割開來。此刻的通俗文本著重渲染,不停延伸枝節,並可以將每個訊息膨脹成情節,陳雪卻極力收減,我發現陳雪「TELL」的部份尤其在於偵查的推動和連環殺人案繁瑣的推演中。這可能來源於,陳雪未必真的那麼知道辦案程序或是推理小說中作者和讀者的閱讀契約,那何不就簡化他。我不知道。我盡量少說。陳雪不作。但這份不作的策略是聰明的,首先,它省力。敘述帶來的簡潔也可以是次要情節的留白,反正你已經知道發生什麼,這每一句被敘述的話語,都可以在未來被解壓縮,留待讀者以想像力或是後繼影像改編者和編劇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開展它。其二,陳雪的「講述」帶來一種速度感。他製造一種動感,更形成動線。讓殺人事件進度飛快,也讓閱讀變成非常爽快的事情。和案情有關的部份都被壓縮了,不妨礙理解,更多時候帶來透明,乃至通透的效果。但這不表示陳雪就完全不「展示」。《你不能再死一次》中所有的「SHOW」留給了小說裡的男女主角,嚴格說起來是衝突──主要是在於男女主角彼此的對手戲,以及女主角之於嫌疑犯的回憶和交鋒上。這樣的「SHOW」是有意義的,總是以情感為主,人性貪瞋癡於往來之中被摧火被點燃引線。於是我們看到陳雪的敘述策略,「TELL」敘述拉出事件的骨幹,而「SHOW」展示著重於主要人物的情感面。TELL,andSHOW,理與情,次與主,骨幹與內容,《你不能再死一次》不是純文學,但陳雪也未必走類型的路,不如說,他不接受類型訂製的分類,乍看歸類為犯罪/推理/懸疑,但他真正想展示的,是人的心──所謂的愛,及愛之惡,他知道自已在幹嘛,重寫了地圖,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二、陳雪控制了「展示」的樓地板面積。這裡便出現陳雪之於通俗文本的第二宗罪。我們一直在討論「展示」,但「展示」的單位到底是什麼?《你不能再死一次》的開端,有人死了。然後男女主角登場了。陳雪為我們講述主角的過去和悲劇成因。這個女孩認識小鎮的第一位死者,父親還被認證為兇手,女孩因此整了型,換張臉便以為可以換掉過去。殺人案懸而未決,小說裡沒人知道女主角過去的臉,但讀者卻從小說第一章開始便對主角的過去一目了然。這樣的開場在本質上就和此刻演進中的通俗岔開來了。在「SHOW」的影像世代裡,通俗文本的中主人公們,是永遠的現在進行式,主角不是沒有過去,而在於,揭露主角的過去,也是一次戲劇化的「展示」。它不能免費給你,它是一枚重要的代幣,在最關鍵的時刻丟進去才能產生777連線的效果。這麼說吧,國王死了,然後皇后死了是故事。國王死了,然後皇后傷心而死是情節。而「皇后死了,為什麼呢?因為國王死了,皇后為此傷心而死。」則是現代通俗的語法。什麼時候告訴我們真相,比什麼是真相更重要。是以通俗文本中的角色不只是角色,也是舞台上機關的一部分。而真正的主角,是閱讀的讀者或螢幕前的觀眾──我們閱讀或觀影追劇時經歷的這一切,像參觀迪士尼古堡或是八卦山大佛裡壁畫,是導覽似的,重點在於「感受的是受眾」,而不是主角。所以資訊必須接受嚴格控管,連「揭露過去」也是引發「感受」的一環。但陳雪不作,他不玩這套,他要製造的,不是這樣一個適當時機告訴我們答案造成翻轉或恍然大悟的翻轉效果。(另一個形容,這其實和恐怖片裡的驚嚇效果同樣原理。適當時機跳出來嚇你。)你可以說《你不能再死一次》是古典的,但毋寧說,小說家陳雪本質上依然還是挺純文學的──他頂著是老派經典那種「人被丟到一個情境裡,看他發生什麼事情?」陳雪不作,他不用碎片化的情節去強行製造懸疑,不是用翻轉好藉由瞬間震懾或感動強行過關的。陳雪建立兩個好立體的人,給你身世,捏了臉,放在舞台上。接下來是看這些人物如何壞掉,或是獲得拯救。當然,這不表示通俗文本中沒有立體的人物。我想強調的是,通俗小說有一個方便法門是永遠展示「現在式」,是尋找何時放出「資訊」的最佳時機,但陳雪捨近求遠,他想展示的是「人」,是未來藏在過去裡,是人在世界經歷各種試煉的天路歷程,他們都在「展示」,但「展示」的單位不一樣了。三、不一樣。題材與寫法上的不純,和技術上的不俗,讓上世紀的惡女變成新世紀的惡人。已為人妻,但不從良,持續作惡中。他怕嗎?當然怕。怕被讀者丟掉,怕讓自己失望。怕走錯路,非常怕。可很奇怪,在寫作之前,很怕,陳雪還是一直寫。《無父之城》、《親愛的共犯》、《你不能再死一次》。邪教。怪奇殺人。密室。詭計。綁架。警察程序。所以,惡為什麼吸引人?這問題在陳雪的身上引出另一個提問是,明明擔驚受怕,創作為什麼吸引他,讓他停不下來?(七夜怪談西洋版裡貞子說:我知道我在傷害人。但我停下來。)我的答案是,因為寫作和犯罪一樣,是一種附魔。在所有我認識的寫作者裡,陳雪是最接近殺人者的那一種。他有一種無情。自我規訓,「我寫到下午就會去運動。每天作一百下深蹲」,他會這樣告訴你,然後站在書桌前開始蹲下又站起,腰腿發達,意志堅定,身體只是具忠實執行工作的機器,能吃苦,好好維護,寫作同時是殺人大業。那種狂熱與意志力的反覆槌打。冷靜而富於執行力。百折不悔。預先查探路線,穿著雨衣伏身被害人家樓下,一次又一次回到書桌前把草稿廢棄重寫,又一個題材完結掉好像名偵探柯南裡黑衣人只露出笑容把筆記本上又一個名字劃掉。我有幸目睹《你不能再死一次》最初的初稿。在那個不停殺人換臉的故事裡──計畫越來越精巧了,事件越是曲折,但有一個核心始終未曾改變。那就是殺人犯的自白。他為她做了那麼多啊,那些漫長的等待,那些無止盡的自棄,那些巧妙安排的殺戮……他等待著她甦醒,然後就要把多年前沒有親口告訴她的話一次說盡……那時他就知道自己恐怕還是沒有能力對她表白,他期待這一天太久了,他無法接受另一次地拒絕,倘若她又拒絕他,他只能將她殺死,沒有其他辦法,可是他不想要她死,倘若她死了,他恐怕就沒有繼續活下去的理由。你可以把句子中的「他」換成陳雪,而把「他」換作「寫作」、或是「小說」,那殺人犯的自白便成為陳雪的自白。「陳雪為小說做了那麼多啊,那些漫長的等待,那些無止盡的自棄,那些巧妙安排的殺戮。」、「陳雪只能將小說殺死,沒有其他辦法,可是他不想要小說死,倘若小說死了,他恐怕就沒有繼續活下去的理由。」純文學必須死。類型必須死。但他們又不會死。陳雪去殺純文學,去殺類型,小說在他筆下繼續活出新的模樣,是屬於陳雪模樣的小說。他不作別人作的,他做他想做的,而這樣一個新小說的誕生,是等著被來日的陳雪再殺一次,繼續殺,繼續寫。陳雪熱愛小說。陳雪熱愛描寫惡。而過度狂熱的愛是有罪的。陳雪依然是那個,如他自己小說所描述的,惡魔的女兒。惡魔的女兒才能創造迷宮中的戀人。迷宮是人的心,惡魔的女兒在裡頭殺戮與救贖。愛的時候有文字,創造與死亡,一次完成。本文作者陳栢青1983年台中生。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台灣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作品曾入選《青年散文作家作品集:中英對照台灣文學選集》、《兩岸新銳作家精品集》,並多次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獲《聯合文學》雜誌譽為「台灣四十歲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說家」。另曾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小城市》,以此獲九歌兩百萬文學獎榮譽獎、第三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銀獎。另出版有散文集《Mr.Adult大人先生》、小說《尖叫連線》。

陳雪《你不能再死一次》新書分享會
+ More 陳雪《你不能再死一次》新書分享會主講│陳雪(本書作者)對談│陳國偉(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優聘副教授暨所長)時間│07/02(六)3:00pm-4:00pm地點│誠品松菸店3FForum《你不能再死一次》是陳雪懸疑長篇小說,逼看傷痕與崩壞的記憶,探討受害者與加害者遺族的人生際遇;對於人性、心理狀態有著深入的洞察。本書以十四年前一場小鎮命案做為開端。十四年前,周佳君與父母住在一片桃花林裡,隨著母親過世,父親開始終日酗酒。某個夜晚,周的好友丁小泉失蹤,兩日後被發現全裸棄屍在周家桃花樹下,醉酒的父親被指認為殺人犯遭收押,最後在獄中自殺身亡,獨留周佳君一人面對鎮民的唾棄和輿論的攻訐……主辦單位│鏡文學參加方式│自由入場,座位有限,額滿為止。聯絡電話│02-66333532備註說明│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購書連結博客來【博客來獨家親簽版】誠品【附誠品獨家藏書票】金石堂Momo有聲書同步發行[博客來][鏡好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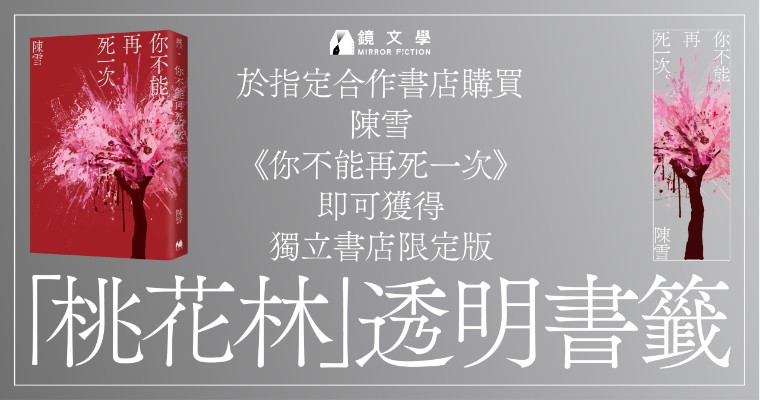
陳雪最新懸疑小說《你不能再死一次》好評熱賣中 送限定版「桃花林」透明書籤
+ More 陳雪最新懸疑小說《你不能再死一次》好評熱賣中!於指定合作書店購買,還可以獲得獨立書店限定版「桃花林」透明書籤(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購買書店這邊請⬇見書店(基隆)https://www.facebook.com/seatoseebookafe/微貳獨冊(台北)https://www.facebook.com/waytoread/櫞椛文庫(台北)https://www.facebook.com/enkabunko/月讀書咖(竹北)https://www.facebook.com/MuMoonReader/島呼冊店(嘉義)https://www.facebook.com/tofubooks/繫.本屋(屏東)https://www.facebook.com/akauwbooks/📖小說簡介📖桃花盛開的時節瀰漫著血色,相隔十四年的殺人棄屍案重現小鎮,被丟在樹下的少女們長出滿樹的衣裙鞋襪,這是她們最後一次的展覽……★繼書展大獎小說首獎《親愛的共犯》後,陳雪最新長篇作品★在殺戮裡發現救贖、不幸之中尋找幸福,再塑陳雪式死亡美學★毀壞後如何長出新的自己?探究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迷離記憶,勾勒人性的光與影

陳雪《你不能再死一次》送誠品獨家藏書票!
+ More 陳雪最新懸疑小說《你不能再死一次》好評熱賣中,現在由誠品通路購買,再送「誠品獨家藏書票」!【購書連結>>>https://reurl.cc/k1bgW3】⬇小說簡介⬇桃花盛開的時節瀰漫著血色,相隔十四年的殺人棄屍案重現小鎮,被丟在樹下的少女們長出滿樹的衣裙鞋襪,這是她們最後一次的展覽……★繼書展大獎小說首獎《親愛的共犯》後,陳雪最新長篇作品★在殺戮裡發現救贖、不幸之中尋找幸福,再塑陳雪式死亡美學★毀壞後如何長出新的自己?探究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迷離記憶,勾勒人性的光與影

寫犯罪,召開一場愛的無力者大會:專訪陳雪《你不能再死一次》
+ More 1995年,陳雪出版《惡女書》。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她還在寫。酷兒先鋒、台妹人妻、戀愛教主、犯罪女王,不同稱號在她身上來來去去。時移事往,許多同輩小說家停筆了,文學地位同時定於一尊,但她還在寫,寫到讓自己疑惑的地方去了。小說家到了天命之年,卻對小說有越來越多疑問。《你不能再死一次》陳雪著出版日期:2022/6/10行過死蔭之地找答案其中一個她必須一再回答、廓清——來自他人,也是她自己的——疑問:為什麼要一直寫懸疑/犯罪小說?《摩天大樓》以降,接連出版《無父之城》、《親愛的共犯》、《你不能再死一次》,用一本一本的節奏挨近犯罪小說的框架;一開始是單純懸疑元素,接著出現偵探查案,最新的《你不能再死一次》更有了連環殺人事件。確實讓人好奇,她孜孜矻矻研磨謀殺巧藝是為何?陳雪的回答是,「為了逼近答案,」她對這答案的回答是「面對罪行我們該怎麼辦?」人性如迷宮複雜,也能同繁星不朽,但人很難專注探索——在這短影音、OTT夾擊,長篇小說讓作者跟讀者都案牘勞形的時代。因此,陳雪說,需要「用犯罪小說的鉤子」讓讀者願意進入迷宮仰望星斗。進入之後呢?「我想知道殺了人,會變成怎樣的人?或者說殺人的動機,有沒有可能殺人者到最後一刻才知道自己為何這樣做?表面上這惡行很極端,但我們不也常常遊走在惡行的邊緣嗎?去探究理解即將走向極端的人,是不是能拉回一些人?」前陣子事件視界望遠鏡拍到了黑洞,陳雪也在做一樣的事,丟出犯罪小說的鉤子到深不見底的地方,悄聲問,還有人在這裡嗎?從「純文學」出發寫懸疑犯罪,陳雪是孤獨的。「寫《摩天大樓》時,有個朋友說他不懂我為何會從《迷宮中的戀人》變成《摩天大樓》,他始終沒告訴我他的納悶是什麼。好友看了我後來幾本小說,只說:『你會的是我不會的。』之後也很難再討論。有一段時間,好像朋友們都不知道我在幹嘛,那段時間我也會懷疑自己到底在做什麼,好像跟好朋友已經不是同一路的人了,我不知道可以跟誰討論小說創作。這種感覺讓我很困惑。後來我只能告訴自己,我是在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只能靠自己摸索。」說完,陳雪想了一下又說,「可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也寫罪行啊。」▲「難道戀愛教主加犯罪女王,就會把小說家陳雪取消了嗎?」這是先行者如她,從「純文學」到類型的大哉問。陳雪寫出了疑惑,也在疑惑中自我辯證答案。(圖/鏡文學)犯罪的美麗新世界不過這句補充透露當我們討論純文學跨足類型,必須很小心,稍不注意就會落入誰主誰次、有尊有卑的二元窘境。陳雪自己也明白,「我很怕自己有寫懸疑小說是在降低自己的感覺,相反的,我是在寫懸疑/犯罪時才發現小說的邊界。」「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類型或犯罪往往被看輕,那它為何很難寫?我自認是專業小說家,還是覺得很難,甚至不斷問自己為何要寫這個,我到底適不適合寫?這讓我思考,答案或許在小說自身。類不類型、純不純文學是小說方法的不同。」「所以問題是,到底是什麼限制了我們去寫(犯罪小說)?」這或許是訪談中這麼多問句裡,陳雪最渴望知道答案的。為了寫懸疑犯罪,陳雪重新學寫對話。這件事過去讓她焦慮,「我們習慣用風格化的敘述推動劇情,但犯罪小說需要對話。進入對話後,角色說話要有個人特色,日常的感覺,不能風格化。同時,對話不像描述,很難用漂亮的文字,只能用基本功。這提醒我戒除對文字的依賴,讓文字更中性。文字不只是服務作者。」犯罪小說仰賴的框架或者說套路,一度也是陳雪的心魔。「我知道要有套路,但常常想不落俗套,所以會陷入猶豫矛盾。」從《無父之城》到《你不能再死一次》,犯罪小說的痕跡更明顯,陳雪的說法是「終於擺脫心裡的包袱」。寫犯罪,表面上是跨界,實際上是再發現,發現小說別有洞天,發現自己還能寫,「我才五十歲欸,還有扣打,可以去學習新東西。」回到植有桃花林的小鎮《你不能再死一次》有個華美的死亡開場,少女陳屍在盛開的桃花林中,「花瓣墜落於發著短草的地上形成一片花毯,花毯中盛開著一張少女的臉。」死亡混著花與青春,禁斷的甜膩氣息。不久,女主角父親被指認是凶手。父親被捕後自縊,她因此家破人亡,遠離家鄉。十四年後,同樣的犯罪手法再度出現,女主角被迫回到家鄉,直面桃花林中的黑暗。相較前兩本,《你不能再死一次》有偵探,有辦案過程。更重要的是,有凶手——一個連續殺人犯——的模樣。陳雪不諱言,寫這本是她創作以來最痛苦的一次,「這本小說的最大功臣是阿早,小說來自他想到的書名,我才從這書名去想怎樣的情形不能再死一次。」過程中,伴侶阿早怕陳雪寫不好,不斷跟她討論,「去年五月我把初稿給阿早看,被他退稿。之後我跟阿早睡前都在討論小說要怎麼寫。他以一個愛人的心情擔心我寫差了,兩邊(純文學與犯罪)不討好,連他都說你還要寫這個嗎?但我是一個很固執的人,所以這本改了五個版本。交稿後我心裡只想,我不想再改一次。」所以,寫犯罪小說,除了擺落文字習慣,學習套路再反套路,陳雪還學到了一件事,「以前我覺得寫小說就是一個人的事,這次的經驗很寶貴,打破了我的想法。」過程中,有件事讓陳雪記憶猶新,「有個段落我一直寫不到位,阿早就放了徐佳瑩的〈人啊〉給我聽——因為我平常寫作只聽古典樂。我是很少哭的人,寫到最後,我哭了。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像演員,在扮演自己寫的角色。這時候我才想到,過去寫純文學我不會脫離自己太遠,但寫犯罪不一樣。」從創作者變成自己創作的角色,這一回,還包括連續殺人犯。「我想寫非一般的殺人者,琢磨這樣的人的心態。以殺人者當第二主角比較少見,所以我放了很多篇幅在這角色上,因為要夠曲折,夠層層疊疊才能逼出罪行對人的影響,又是什麼導致的。」陳雪的創作姿態,讓我想到英國作家薇兒麥克德米。同是女同志,同樣書寫謀殺,描摹暴行。薇兒麥克德米過去常被非議,為何要寫得這麼殘忍呢?自稱見血會昏倒,卻努力在小說裡殺人的她回道,女性本來就生活在危機四伏中,時時都有可能遭受侵犯。因此,女性書寫犯罪更能從當事者角度感受,並度人以這感受。▲為何持續寫懸疑/犯罪?陳雪還有另一個更直覺的答案,「以前寫小說像在修復自己,把自己修好了要做什麼?結果是寫謀殺。這個呼喚非常強烈,就像我已經準備很久了。」陳雪說自己不熬夜,努力吃得好睡得好,都是為了專注寫小說。彷彿身體是一座神殿,唯小說供養。(圖/鏡文學)再狂野追尋一回回到陳雪,她更從加害者的角色出發,帶給讀者原來愛恨互為表裡。這也回到一開始陳雪的疑惑,戀愛教主為什麼一再操演犯罪?「很多讀者習慣看我的臉書寫戀愛故事,可是讀完那三百字後,就像喝雞湯也不會長肌肉。不被愛,不愛自己小孩,因為愛做了錯誤決定,或者愛怎樣拯救自己,都是讀小說才能有的體悟。」陳雪是小說之神鍾愛的女兒,因為她仍信仰小說的力量,「小說讓我們擁有無法度過的人生,透過閱讀,你逐漸經歷別人的人生,而被改變。即使你從小到大都待在一個很小的地方,讀了很多小說,你就能穿透世界。」因此,陳雪左手寫戀愛課散文,右手寫出《無父之城》是小我的愛遇到國家級暴行的下場;《親愛的共犯》是彼此相助如珍珠項鍊般串鏈的珍貴之心;而《你不能再死一次》則是當愛被誤譯的悲劇。陳雪坦言,一開始不大喜歡戀愛教主跟犯罪女王這類標籤,「但後來我覺得也滿酷的,而且它們是有共通的,都是關於愛的想像。小說裡,我儘量讓讀者可以找到一個站立的地方,不要站在流沙上。回過神,人會發現自己是可以穿越這些殘酷無情的。」一手寫戀愛,一手寫不被愛,需要精巧而調節的平衡感。陳雪說,現在的穩定生活,給她這樣的寫作力量。「以前的我沒辦法達到這種平衡,因為以前我就是談戀愛與無止盡的幻滅,不斷找下一個人。我會想,難道人只能互相勾引,狂愛後背叛、分離嗎?難道愛情沒有另一種可能嗎?這樣想才意識到,我以前的生活也是一個套路啊,我用現在的生活證明了,人可以反自己的套路。」訪問前夕,陳雪以《親愛的共犯》獲書展小說獎大獎。我問她有何感受,陳雪回答,得獎讓她覺得好像可以再寫一本;寫犯罪,終於感覺自己不是出界了,而是在拓展身為小說家的邊界。邊界落在哪?小說家其實走過。陳雪說了一段故事,「前陣子《惡魔的女兒》重出,我才發現裡頭都是對話,阿早就說不是你不會寫對話,只是忘記了。我想對啊,如果世界上沒有我的價值,我應該要自己定義。當初《惡女書》連出版都差點沒辦法,為什麼我到了五十歲,寫東西要綁手綁腳?我應該再大膽一次。」這次訪陳雪,是我聽過受訪者丟出最多疑問的一次,也是透過疑問獲得最多力量的一次。我想起羅貝托博拉紐一首關於偵探的詩,遙遠回應了陳雪不斷探問的小說的邊界:「我夢見迷失的偵探/在阿諾菲尼夫婦家的凸鏡裡:我們的時代,我們的視角,我們的恐怖模型。」我們的時代,我們的視角,我們的所懼怕的,都構成了小說家的邊界。陳雪是博拉紐夢見正尋尋覓覓的偵探。

黑夜總會過去的 ——Kristin讀陳雪《你不能再死一次》
+ More 「那時他們的屋子後半部每一扇窗戶都可以看到桃花林,每一年春夏秋冬,她看到綠樹發芽,開花,結果,然後到了落葉時節,一切變得蕭瑟,有一次他們全家在窗前看落葉,父親去清掃葉子,把樹葉堆起來燒掉,她覺得悲傷,父親卻對她說,『冬去春來,人生就是這樣輪迴輪換,所以遇到壞事不要緊張,春天一來就會萬物復甦了。黑夜總會過去的。』」故事的第一章,猶如電影的開場,一名美麗的少女陳屍於桃花林中,白色、血跡、花瓣與與赤裸的身軀形成奇異之美,伴隨著逐漸膨脹的恐懼感。作家陳雪的長篇推理新作《你不能再死一次》,透過如此流暢清晰的影像文字,為這齣橫跨多年的連續殺人案件揭開序幕。故事以此為核心,圍繞著第一場命案的幾名核心人物,抒情與敘事並重,從人性層面切入,他們伴隨著各自的心魔辛苦長大,長成了孤獨封閉的大人,多年後,命運將這些人帶回起點,試圖釐清血案背後淒美而殘酷的真相,摸索屬於自己的生命出口。當年的三人組丁小泉、宋東年與周佳君,一個二八年華便不幸香消玉殞,留下過於自責的初戀男友,以及眾人口中「殺人犯的女兒」的摯友;十四年轉瞬即逝,一切不因草草結案而落幕,宋東年選擇走上警察一途,行屍走肉般埋首工作,而周佳君則徹底改頭換面,變為業界知名的犯罪案件專題記者李海燕,不斷從他人的悲劇中探詢解答,關於悲劇,關於哀慟,關於餘生。《你不能再死一次》陳雪著出版日期:2022/6/10善惡的分野如此從人性面出發的推理小說,必得重新挑戰觀眾的道德天秤,是與非、善與惡、光與影、生與死、美與醜、愛與恨,一切是對立存在的,但於《你不能再死一次》中,每個當局者皆有自己的思考模式,長期處於灰色地帶,唯有跳脫世俗觀點的枷鎖,方能挖掘到真正的情感真相。「追悔會成為他們餘生的命題嗎?一樁命案可能把一個家庭或數個家庭完全摧毀,還活下的人,都變成什麼樣子?」對於李海燕而言,若想釐清生命裡沒有解答的問題,好比被視為畏罪自殺的父親,最可行的方式是主動接近、理解罪犯,試圖從他們的角度看世界的過程。至於宋東年,偵破無數案件卻始終無法揉開內心的瘀血,遍尋不著自我救贖的途徑,真正吞噬他的,更像是那份難以和死亡抗衡的無力感。另一方面,相較於揪出兇手,該如何挖掘犯案動機、還原完整真相,那也是「抒情寫實」的訴求,選擇探就心理層面的原因與影響,企圖映照社會與大環境的陰影。總說悲劇的發生,並非單一原因使然,而是一連串的不幸所導致。事實不出人人都是自己故事中的主角,擁有自己版本的真相,以及與世界應對的方式,陳雪透過核心角色各自的來時路,透徹梳理成長過程與外在環境對人格特質的影響,非為罪刑開脫或卸責,而是可恨之人往往有可憐之處,彷彿背對陽光,凝視著深淵,折射人性難以被定義的多樣性,在揭開謎底的同時企圖審視挫折根源,並憑藉文學的力量尋找些許理解與同理。創傷記憶「無論對受害者或加害者而言,創傷記憶本身就是一種創傷,因為重溫記憶使人痛苦,或難免讓人覺得不適。承受傷害者傾向於壓抑記憶,以免再度感到苦痛;傷害他人者則傾向將記憶深埋心底以求解脫,同時減輕自己的負罪感。」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普利摩李維於著作《滅頂與生還》如此談論,單單是「記得」,就得不停與社會、親人、自我、記憶對抗,親眼見證創傷對人性帶來深遠的影響,且記憶會有意識且無意識地牽動我們的過去、現在、未來。所以阮越清會寫,所有戰爭都發生兩次,一次在戰場上,一次在記憶裡,那些終其一生不停遺忘的過往。於此書中,陳雪再度透過類型小說探討了「創傷記憶」這個龐大命題,宋東年、李海燕深受童年陰影與命案所苦,顯現於後來種種沉默、封閉的性格特質中,他們單打獨鬥拚命遺忘,卻不停被拉回過去,生命狀態自十六歲起便陷入停滯,時而壓抑,時而逃避。然而,較為幸運的,愛與命運讓他們用不著繼續承受獨自一人重新開始的苦痛,李海燕鑿開了宋東年的冰封許久的內心,宋東年則一再用行動證明渴望共同重建生活的決心,而治癒的契機,就始於真正感受到「沒有人是一座孤島」。畢竟沒有一種酒,可以讓人從此醉生夢死,沒有一種恐懼,可以於時間中煙消雲散,一旦捨棄記憶,就會忘記自己原本的模樣,時間無法沖淡過去,只能找到一種方式與其和解,與之共存。愛永遠比恨更強大假使人們持續對惡避而不談,也會忘記愛有救贖力道。《你不能再死一次》作為推理小說的名稱,顯示了於此齣連續殺人案件中,即便犯下滔天大罪,即便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記,愛仍是唯一的解答。因此,在分隔這麼多年,李海燕與宋東年依然扮演著彼此的解鈴人;自幼缺乏關愛的高岸,畢生受一廂情願的情感所趨動、所左右,但偏偏多數時候,真正的愛不是做了什麼,而是選擇不做什麼。「他說是為了愛,或許是吧,他畢竟也付出了代價,用錯誤的方式去愛人。」故事的末端,教人想起濱口龍介的《在車上》,最後於《凡尼亞舅舅》的舞台上,允兒流露堅定神情比劃著:我們要繼續活下去,我們一起走過漫漫長日,穿越幽幽的夜晚吧!咬牙承受著命運的考驗,無止盡地生活下去,在回望自己吃過多少苦、流過多少淚的最後一刻,將得以帶著微笑,平靜休息。在得到與得不到之間,可窺見愛有摧毀的力量,同時有彌補的力量,這也是陳雪反覆透過小說琢磨的複雜性。海燕感受到的愛與苦難亦是如此,難以名狀,無從釐清,有時相伴同行,已經一起經歷了這麼多的風風雨雨,他們未來即使有更多的漫漫長日、幽幽夜晚,亦不足為懼,曾經世界一片漆黑,當出現一道光線劃破黑夜,即使微弱,即使稍縱即逝,光明仍戰勝了黑暗,他們也將重獲新生,見證著悲傷的美麗與意義。本文作者Kristin東吳中文畢業,英國UniversityofSheffield國際行銷碩士,以推坑無數的書評和影評見長。經營粉絲專頁「一頁華爾滋LetMeSingYouAWaltz」,取名自電影「愛在三部曲」中第二部《愛在日落巴黎時》的音樂曲目。透過輕輕觸摸卻相當深刻的口吻,投射自身人生經驗,解讀潛藏於影像、文字和現實世界底下那人與人以及人與自我之間的關係。在探索人類情感的旅途中,以真摯且獨特的體悟、感知和目光解讀眼底那片文學與電影的星空,並給予讀者無比溫暖的答案,讓人們在負傷之際能片刻喘息,讓人們在愉悅之時能閒適自得。選擇鍾愛的文字作為媒介,溫柔感受生命的每一個瞬間,細膩品嘗虛實交錯的真實生命經驗。FB:一頁華爾滋LetMeSingYouAWaltzIG:kristinswaltz相關著作:《光影華爾滋(獨家限量作者親簽版):每部電影,都是一支擁抱內心的迴旋舞》

死亡的理由:陳雪小說創作的新本體——陳國偉評《你不能再死一次》
+ More 陳雪一路從1990年代走來,以酷兒小說家出道,開啟了性別書寫的新局。接著在21世紀之交,她展現出鄉土的書寫手藝,重述了自己的起源故事;後來她成了同婚的先驅,也跨足愛情散文的書寫,展現出多元的創作能力。然後時間前進到2015年,她在「當代小說家」這個具有典範象徵的書系,交出了讓讀者與評論家既驚艷但又略帶困惑的《摩天大樓》,自此進入了她全新階段的死亡書寫。在她過去的創作中,當然不是沒有涉及死亡,但後續一連串《無父之城》、《親愛的共犯》到最新作《你不能再死一次》,死亡被置放在故事的核心,成為運轉小說世界的主要驅動力,甚至在形式上向推理犯罪類型靠攏。這麼劇烈的蛻變,不禁讓人思考起,在進入21世紀20年代的今天,陳雪書寫死亡的全新嘗試,對於台灣的小說創作,將會帶來什麼意義。《你不能再死一次》陳雪著出版日期:2022/6/10一旦談到小說與死亡,我們總不免想到推理犯罪類型,也總是會聯想到那些經典的名字,《謀殺與創造之時》、《謀殺巧藝》、〈血字的研究〉……死亡是一門學問,但當它被想像成專屬於一個類型,並追求一種美學的雕鑄、技藝式的錘鍊時,其過程與原因往往被謎面化為折曲的探問,彷彿必須遠離死亡才能再回返其自身。而書寫這一切的人,也被想像為擘畫犯罪的藝術家,死亡被暫時擱置哲學式的終極意義探問,而被安放於一個敘事秩序之中,故事最終必得解開死亡的理由,彷彿那便是死者以及環繞在其身邊人物的唯一意義。然而,這不僅是對小說與死亡之倫理性的蒼白想像,也是對極盡死亡奧義的推理犯罪類型之偏狹認知。因為,正如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中指出的:「小說人物的『生命意義』只有在死亡的一瞬才顯露。但一部小說的讀者確實是在尋找他能從中獲得生命意義的同類,因此,無論如何他必須事先得知他會分享這些人物的死亡經驗,若有必要的話他們象徵性的死亡——小說的結局。但更佳的是他們真實的死亡。人物怎麼才能使一位讀者明白死亡在等待他們,一個確切的死亡,在一個確定的地點?這是個永保讀者對小說事件濃烈興趣的疑問。」可以說,死亡其實正是小說這個文類的本體,死亡既是小說的第一義,也是其最終意義。所以,敘事與書寫,作為死亡逃逸策略的隱喻,如《一千零一夜》那樣,彷彿只要故事的歧徑花園足夠複雜,便能幻化為一個又一個的迷宮,抵禦死亡的到來,將其困住拖延,讓讀者能夠期待小說人物的生命旅程抵達到最後。而犯罪推理小說與非類型的差異其實僅在於,一般小說往往將死亡懸置於最後,但推理犯罪類型從一開始就直面了死亡。也因此,無論是對於故事象徵性的死亡(小說的結局),抑或是小說人物真實的死亡(一個或複數以上的死者),在推理犯罪小說中,為何必須要死?如何會死?就成了敘事的主要關懷。小說人物的生命意義不僅只在死亡的瞬間顯露,而是在整部故事的過程中展演,在「預知死亡紀事」啟動了情節的齒輪後,如何在死亡預演的陰影中,探照出角色生命的每一個角落,無論是透過關係人的陳述,還是偵探或解謎者的偵察與探勘,小說的敘述過程其實是人物生命卷軸緩緩展閱的歷程,而且不僅限於死去的人物,也含括了所有在故事中的角色。所以,推理犯罪小說的聚光燈不是只在偵探、犯罪者跟死者身上,而是如同鏡宮一樣,讓所有角色彼此對映的重層鏡象。而這,正好是陳雪這一系列死亡書寫中的核心。綜觀台灣純文學與大眾文學領域,要論描寫人物,特別是透過內在的生命與創傷經驗,立體化人物的形象,陳雪絕對是數一數二的佼佼者。而人物,不僅是故事的靈魂,更是推理犯罪故事中,在那複雜的人際網絡間,牽動所有角色行動與情節推演,甚至是決定整個小說世界躍昇或沉淪的關鍵。從《摩天大樓》到《親愛的共犯》,陳雪往往透過結構上角色的自我現聲,架起人性無法匿藏的鏡宮,透過角色之間的相互映照,透亮所有人物生命與性格的暗影與羅網,最終推演出她意圖辯證的罪與罰。然而到了《你不能再死一次》,身為說故事者,陳雪的技藝更為純熟,她以故事整體的經緯,將角色的內在聲音與事件的外在陳述巧妙地鑲嵌,讓複線交織的情節精準地推移,因而無論在小說的內外層敘事,或是人物內面的複雜性上,都創造出更多的意外性與驚喜。不僅如此,死亡其實是有時間性的。推理犯罪類型中的死者,無論是偵探的再三探問,或是關係人的往復回憶,在那些敘述與對話中,逝者都會重複地再死一次。而即便是生者,也如雷蒙‧錢德勒在《漫長的告別》裡的那番抒情的宣言:「告別就是死去一點點」,死亡的時間性在每個角色的任一行動與決定中,其實早已反覆地啟動著。也因此陳雪這次不只描寫一次性的死亡,而是連續的兇案,透過調度生與死的複數時間景觀,讓小說中生者與複數死者相互漸層與浸染的真實生命圖景,以及人性善惡維度的複雜性,隨著連續疊合共構的時間景觀,彼此共振。然而更重要的是,死亡不必然是最大的傷痛與真正的懲罰,陳雪在這系列的書寫中一直希望傳達的,便是這種在世存有的煎熬與自我試煉,無論是生者或死者,無論是犯罪者還是找尋真相的人,在這個死亡羅網中,那些深埋在生命紋理的慾望湧動、遺憾、後悔、罪愆與懲罰的創傷鑿痕,會隨著時間永遠無限地延滯,不斷地復返降臨。因為許多傷痛、慾望與惡意是沿著血緣而來,因此那些痛楚隨著呼吸反覆震盪,是既想擺脫但又沉溺其中的原初驅動,遺棄╱遺忘與欲求╱慾望實是鏡象與孿生的一體兩面。陳雪也許沒有言明,但這一切在小說中其實已經呼之欲出的,是人的怪物性,或者說,惡魔性。承載死亡的敘事總是能夠透過美學的追尋召喚出人的怪物性,因為殺戮,因為憎恨。但透過「連續死」與「勉強活」的小說人物對位,陳雪讓我們意識到,真正的怪物不只是犯罪者,而是因死亡的理由而催生出的所有存在,那些被愛與恨的糾葛掩映的影子,就是怪物的棲身之所。人與非人不是一線之隔,而是互為主體,隨時轉化。只要點燃愛與恨的動能,就能驅動人流變為怪物,甚至成為惡魔。陳雪希望提醒我們,正如她一直以來的關懷與觀察,家庭其實是怪物與惡魔最原初的產地,那些創傷與犧牲者,總是在以愛為名的惡意中被餵養成怪物,甚至只要你忠實於自己的慾望與傷痛,就可能隨時在鏡象中,看到自己那張惡魔的臉。最終,唯有面對這一切,救贖與理解才可能到來。當妳╱你閱讀到《你不能再死一次》的最後兩個章節,方能懂得陳雪的苦心孤詣。而這,是她書寫死亡真正的理由,也是她對小說本體的新一階段思考,更是她小說創作生涯,讓人期待不已的新境地。本文作者陳國偉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優聘副教授暨所長

人間哪有凡爾賽 看職業小說家甩斧頭——楊隸亞評陳雪《親愛的共犯》
+ More 夢幻豪宅殺人案很久沒有這樣的感覺,捨不得讀完一本小說。陳雪近年曾說要完成小說三部曲計畫,分別是一座大樓,一座城市,一座小島。從已出版的長篇小說《摩天大樓》(2015),《無父之城》(2019)來看,小說家真的說到做到,《摩天大樓》讓讀者窺見水泥森林裡都市人類內心的孤獨荒涼,《無父之城》走入小鎮尋找身世命運與歷史記憶流變。這次,最新長篇小說《親愛的共犯》(2021)小說家的眼睛同樣凝視著「空間」展開,豪宅vs育幼院,富有vs貧弱,空間的對立感所營造的階級群像也不停指引(誤導)讀者,讀至最末章仍在真相邊緣打滑繞圈。《親愛的共犯》陳雪著出版日期:2021/1/29《親愛的共犯》全書有四章,分別是:夢中人、沉睡者、追擊者、守護者。在懸疑小說的推理架構底下,透過整部小說的靈魂人物——女警周小詠,走進豪宅與育幼院,撥開層層雲霧尋兇辦案,也透過她的雙眼顛覆傳統定義的空間價值、家庭組成、愛情觀念。這部小說該要垂直去看,看山坡上,看市中心,還有,看流浪天涯四方,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小說開始就花費大量的篇幅做空間造景,故事出現兩棟強烈對比的房子,一棟是山坡上的育幼院,另一棟是位於市中心黃金地段,別名為「白樓」的高級豪宅。育幼院裡的孩子三餐僅是溫飽,多人共用狹窄的客廳廚房,煮飯打掃雙手萬能,雙層上下床舖,一張床還得擠著兩個孩子,他們用自己的塗鴉繪畫和生活照片裝飾點綴牆面,手牽手甜蜜的像真正的家人。而另一棟「白樓」豪宅,從設計動線到建築美學,清水模構造現代主義,以為安藤忠雄到此一遊,兩旁盡是獨家展品,搭乘電梯往上升,一層一戶,司機外傭阿姨服務到位,採光入屋,卻不入心,滿滿的冰冷。小說家陳雪以豪宅主人張大安最疼愛的二兒子張鎮東被綁架勒索為故事開端,展開一連串警方與殺人犯的諜對諜攻防戰。台灣的宮部美幸二月上旬,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的陳國偉所長於「開房間」(ClubHouse)app發起『台灣宮部美幸,襲來!?』的類型小說討論,他指出以下概念:日本一直有『國民作家』的傳統,最年輕的一位,正是多數讀者相當熟悉的宮部美幸,而台灣作家陳雪近年交出的長篇小說作品,如《摩天大樓》、《無父之城》到《親愛的共犯》,書中處理角色人物與社會議題的手法,都讓人聯想到宮部美幸。老實說,閱讀《親愛的共犯》過程中,陳雪處理死亡與掩蓋秘密的指向,比起「技術指向」,更多的確實是一種「情感指向」,讓我有那麼一瞬間想起日本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在《嫌疑犯X的獻身》裡面所創造的「愛的犧牲」。多年前,《嫌疑犯X的獻身》究竟是否屬於「本格派」推理小說,曾引起不少討論。小說裡的愛意,一個人可以為世界上另一個人付出到什麼程度?比起數學推理,擺在面前的是巨大到令人惶恐的愛。不過,X一書確實更偏向「時間秘密」的機智解謎,《親愛的共犯》雖然也製造出類似「時間秘密」的手法,卻不是通往真相的唯一路徑,比較像是聲東擊西,用來阻擋、轉移人們視線的障眼法。如果說推理可以拆成兩條思維,一條是合理,一條是合情,《親愛的共犯》更接近後面那條「情之路」,情多於理,刻畫人性多於解謎刺激。這並非意味小說在推理結構不夠慎重緊密,而是比起武功技藝,或許小說家更期待讀者能夠把人物的內心世界看清楚。當讀者依循小說家拋出的各種線索,條件紛紛指向「群體犯罪」,甚至就要大膽斷言這是一場類似「東方快車謀殺案」,一人捅一刀的大團圓套路犯案。最後一章,陳雪再度讓你大吃一驚,事情完全不是看上去那麼單純。因此,要細講起來,比起本格派的出手,陳雪在《親愛的共犯》所要展現的,確實更接近宮部美幸那般,往「社會派」的方向傾斜,比起享受解謎鬥智的刺激感,更多是一拳打在你心臟胸口上人性試煉的重擊。看職業小說家甩斧頭村上春樹固定慢跑,宮部美幸喜歡打電動,陳雪則是每天吃完早午餐後,下午固定寫長篇小說,1500至2000字左右,每週規律做瑜伽,晚上深蹲加追劇。過年期間,聽說只休除夕跟大年初一,每天都寫,從不間斷,高度自律的她曾表示,當日小說進度完成之前,絕不開臉書。我想起村上在《職業小說家》裡曾提及:『小說家的賞味期限——頂多十年左右吧。超過這個期限之後,就必須有更大的、永續的資質,來代替頭腦的靈活了。』他還舉例小說家的進程是三把銳利的刀,剛起步的小說家有「剃刀的鋒利」,往後能演變成「柴刀的鋒利」,最後抵達「斧頭的鋒利」。能夠順利轉換下去,即是戰勝自己存活下來的小說家。回想陳雪的第一本小說集《惡女書》(1995),時至今日已過26年,如今的陳雪,是否已走到村上春樹在職業小說家分類裡,傳說的「斧頭刀」等級呢?本次新作《親愛的共犯》有一段描述,特別動人:『當時他們四個人,曾經說好永遠不分離,好像這世界上只剩下了他們,所以他們必須好好地守護著彼此。在那片山坡上,李安妮說過她將來要當歌星,林曉峰說他要當太空人,崔牧芸呢?她說她想要當護士,只有陳高歌,什麼願望也不肯許,或者他想過了但他不肯說出來,當大家鬧著要他說的時候,他就說了,「希望我們永遠是一家人。」這樣自立自強,只能依靠意志力建造夢想的孩子,讓我想到陳雪的短篇小說集《橋上的孩子》,裡面有一個家庭經濟陷入困境,被生命逼迫長大的少女。我也曾在不同的文學場合,書展講座或文學營聽過陳雪提起一段故事,那是關於小女孩在一棟如同迷宮的旅館裡尋找母親的故事,母親就藏在某一個號碼的門背後,這段尋覓之旅也是尋愛的渴望、孤寂、脆弱。從前,在迷宮旅館尋找母親的小女孩,在夜市擺攤叫賣衣服或批發手錶送貨,夜裡抓緊時間瘋狂寫小說的少女,赤足踩刀一路走來,如今成為職業小說家陳雪。她不再需要取下身上的羽毛來當作故事題材,一出手就是一個全新的世界。本文作者楊隸亞一九八四年十月生,台北人。東海大學中文系,成功大學現代文學碩士畢,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聯合報》文學獎散文評審獎及懷恩文學獎、桃城文學獎等其他獎項。作品散見各報副刊、《印刻文學生活誌》、鏡傳媒等。

哪一種才算是家,的推理——張國立評《親愛的共犯》
+ More 大部分推理小說總是在死了一個人之後開始,忽然想起大導演雷利.史考特(RidleyScott,代表作有《銀翼殺手》、《異形》、《王者天下》、《黑鷹計畫》、《神鬼戰士》)的《末路狂花》(Thelma&Louise),關於塞爾瑪與路易絲兩個女人的故事。她們本來過著平常日子,塞爾瑪是個家庭主婦,有個易怒的老公,路易絲則是餐廳服務生,有個不太確定關係的男友。這天,天氣不錯,路易絲心情很好,邀塞爾瑪出去玩,塞爾瑪不敢對丈夫說,可是她決定該出去走走。所以這也是關於旅行的故事。旅途永遠不可能平順,在酒吧外,塞爾瑪險些被男人強暴,路易絲一槍幹掉那男人,旅行變成逃亡。接著塞爾瑪遇上帥哥騙子(布萊德.彼特飾演)而被偷走了她們所有的盤纏。她覺得對不起路易絲,持槍搶了商店,這下子她們再成了搶匪,從調查局到州警動員大批警力的四處圍捕。記憶最深刻的是當塞爾瑪被布萊德.彼特偷走了錢,那是上午,其他人仍過著正常生活,可愛的塞爾瑪卻成了搶匪。她的搶,純粹為了繼續旅程,繼續她終於明白的「存在」。原以為挺絕望,但塞爾瑪終於從丈夫的束縛裡掙脫出來,路易絲也了解男友對她的真愛,「末路」充滿歡樂,她們享受每一刻。《親愛的共犯》陳雪著出版日期:2021/1/29法國著名的推理小說家奚默農(GeorgesSimenon,1903-1989)寫過一個短篇小說《警探回憶錄》(FromMaigret’sMemoirs),故事的主角是名巴黎老警員,他穿釘鐵片的大頭靴天天巡邏於市區,之所以穿大頭靴,是一來警察的薪水買不起好鞋子,二來每天得走十三至十四小時的路。他說,警察的工作和街頭妓女差不多,都有雙得走上幾英哩柏油路的鞋子與疼痛的腳踝。他的工作當然是破案,長官交給他一把凶刀,設法找出凶手,於是老警員帶著凶刀出門,九個月後在某家文具行問出凶刀是這裡賣出的,而老闆還記得買刀的人。他靠堅持與耐心破案。奚默農透過老警員的眼睛帶領讀者看那時候的巴黎,看著初進城的青澀少女隨歲月變成目光渙散的老妓女、看著火車站內找機會的盜賊。推理小說便在生活裡尋找蛛絲馬跡,設法找出答案。奚默農寫,當時巴黎警察兩個特徵:穿大頭靴是因為待遇低,這種鞋子耐走;留大鬍子的起源不明,但大多數年輕人加入警界就是想留大鬍子,覺得酷。讀者隨著大頭鞋同時也進入警察的日常生活,人物像在定格的畫面停留好幾分鐘,然後突然間走起路、說起話。雷蒙.錢德勒的《大眠》,嫌犯卡門小姐到偵探社找偵探馬羅,他們之間有段對話。「幹這一行(偵探),如果你誠實的話,賺不到什麼錢。如果你有門面,那表示你賺了錢──或者準備撈一筆。」馬羅這麼介紹自己的辦公室。「噢,你誠實嗎?」卡門一邊打開皮包一邊問,她從一個法國製琺瑯盒裡取一根菸,用一只口袋型打火機點火,然後把琺瑯盒和打火機丟回皮包,任由皮包開口。馬羅回答,「誠實得很痛苦。」馬上了解馬羅是什麼樣的偵探,了解他的日子不太寬裕,而找上門的女客戶則有錢到滴油。以《後車廂輓歌》(TrunkMusic)創造出著名偵探鮑許的麥可.康納利(MichaelConnelly)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偵探的工作,不再古典時期的優雅,非常冷硬時期的寫實。鮑許談到偵探的工作:「有個雕刻家,當別人問他怎麼把一塊花岡岩變成一尊美女雕像?他說他只是剔除不屬於女人的部分。我們現在要做的也是一樣。」偵探得拿著小鑿子對花岡岩一點點的敲,不能太用力,萬一敲太多,黏不回來的。好看的推理小說必從人性著手,一如巡邏警察偵破殺人案於他的日常、靠他的每一步,這是他的人生。一如拿破崙部下說:「皇帝打勝仗靠的不是我們的刺刀,是我們的腳。」陳雪的《親愛的共犯》一方面女刑警周小詠追查殺死富商二子張鎮東的凶手,一方面作者追查到底「家」該如何定義?真正的家在哪裡?為此,陳雪詳細介紹豪門張氏一家三代居於一棟低調豪宅白樓內的生活點滴,大家長張大安原想這樣能凝聚家人的感情與力量,卻忘記錢畢竟是萬惡之源。錢未必可怕,錢帶來的勢利與階級才可怕,稍稍處理不慎會帶來大禍。這三代糾葛不清的恩怨情仇便是故事的大背景。同時,作者暗示:少了愛,這是家嗎?另一群成長於育幼院的年輕人,他們未忘記當年以院為家培育出濃郁革命感情,彼此關照,當其中一人有難,其他人不顧一切的設法為之解脫。作者再暗示:這樣的感情不算家嗎?透過女刑警的不懈的偵查,她帶出一個人物串接一個人物,帶出每個人的故事,像是拿破崙手下的法國大軍,所有人物奮力的前進,抵達戰鬥位置,組成綿密的戰列,等著作者下最後的攻擊指令。《親愛的共犯》追查的是我們究竟該認同哪一種的家。人生百分之九十處於大多數人認同的軌道上,像丹尼斯.勒翰(DennisLehane)在《黑暗,帶我走》(Darkness,TakeMyHand)裡說的:「他們在人生中載浮載沉,如同浮在熱水上的塑膠鴨,有時會翻側到一邊,等到有人把他們扶正過來,他們又回復先前的載浮載沉。他們不吵架,也沒有真正的熱情。」張鎮東對家人施暴,對事業、對家庭只有要求而不無付出,家裡的親人設法掩蓋事實,像把翻側的塑膠鴨扶正,他們有錢有地位,卻不知道自己失去了熱情,那麼鴨子的倒或正有何區別呢?女警探周小詠找出凶手,然後呢?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塔斯這麼做結論:「尋找真相時,要對不可預期之事有所準備,因為真相總是如此難尋,而且總是在你尋獲時困擾著你。」想到某本小說裡說的:「問題不在於你能不能找到真相,而在你能承受得起真相嗎?」本文作者張國立知名作家/美食、旅遊達人/擅長推理小說、歷史小說等。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曾任《時報周刊》總編輯,得過國內各大文學獎項與金鼎獎,文筆既可詼諧亦可正經,作品涵蓋文學、軍事、歷史、劇本、遊記等各類題材。近期作品:《乩童警探:偏心的死刑犯》、《炒飯狙擊手》、《金陵福史上第二偉大的魔術師》、《海龍改改》、《一口咬掉人生》、《戰爭之外》、《鄭成功密碼》、《張大千與張學良的晚宴》、《棄業偵探:不會死的人,一直在逃亡的億萬富翁》、《棄業偵探01:沒有嘴巴的貓,拒絕脫罪的嫌疑犯》、《偷眼淚的天使》……等。小說《炒飯狙擊手》已售出北美、尼德蘭(荷蘭)等國外版權。
客服時間:週一 ~ 週五10:00 - 18:00(國定假日除外)
客服電話:02-6633-3529
客服信箱:mf.service@mirrorfiction.com
© 2025 鏡文學 Mirror Fic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鏡文學 App
好故事從這裡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