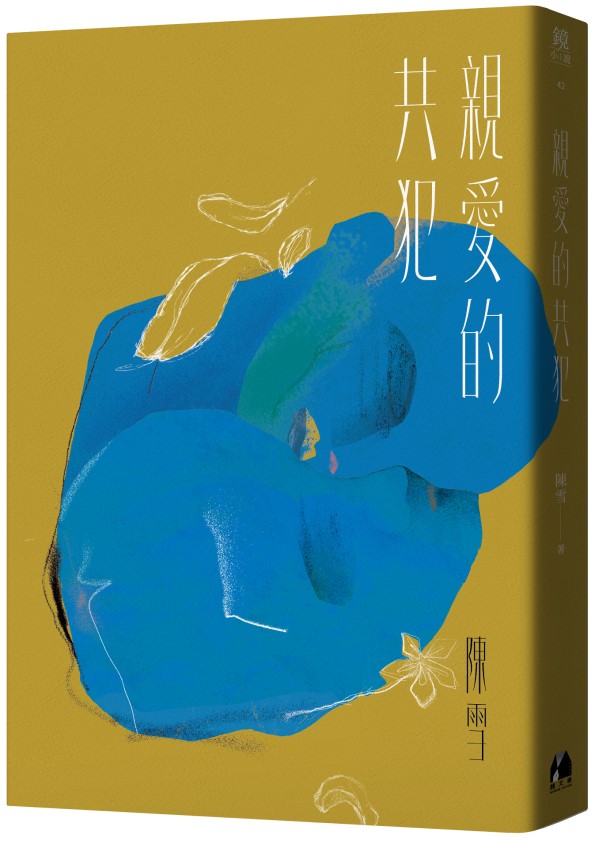大部分推理小說總是在死了一個人之後開始,忽然想起大導演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代表作有《銀翼殺手》、《異形》、《王者天下》、《黑鷹計畫》、《神鬼戰士》)的《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關於塞爾瑪與路易絲兩個女人的故事。
她們本來過著平常日子,塞爾瑪是個家庭主婦,有個易怒的老公,路易絲則是餐廳服務生,有個不太確定關係的男友。這天,天氣不錯,路易絲心情很好,邀塞爾瑪出去玩,塞爾瑪不敢對丈夫說,可是她決定該出去走走。所以這也是關於旅行的故事。
旅途永遠不可能平順,在酒吧外,塞爾瑪險些被男人強暴,路易絲一槍幹掉那男人,旅行變成逃亡。接著塞爾瑪遇上帥哥騙子(布萊德.彼特飾演)而被偷走了她們所有的盤纏。她覺得對不起路易絲,持槍搶了商店,這下子她們再成了搶匪,從調查局到州警動員大批警力的四處圍捕。
記憶最深刻的是當塞爾瑪被布萊德.彼特偷走了錢,那是上午,其他人仍過著正常生活,可愛的塞爾瑪卻成了搶匪。她的搶,純粹為了繼續旅程,繼續她終於明白的「存在」。原以為挺絕望,但塞爾瑪終於從丈夫的束縛裡掙脫出來,路易絲也了解男友對她的真愛,「末路」充滿歡樂,她們享受每一刻。

《親愛的共犯》
陳雪 著
出版日期:2021/1/29
法國著名的推理小說家奚默農(Georges Simenon, 1903-1989)寫過一個短篇小說《警探回憶錄》(From Maigret’s Memoirs),故事的主角是名巴黎老警員,他穿釘鐵片的大頭靴天天巡邏於市區,之所以穿大頭靴,是一來警察的薪水買不起好鞋子,二來每天得走十三至十四小時的路。他說,警察的工作和街頭妓女差不多,都有雙得走上幾英哩柏油路的鞋子與疼痛的腳踝。
他的工作當然是破案,長官交給他一把凶刀,設法找出凶手,於是老警員帶著凶刀出門,九個月後在某家文具行問出凶刀是這裡賣出的,而老闆還記得買刀的人。他靠堅持與耐心破案。奚默農透過老警員的眼睛帶領讀者看那時候的巴黎,看著初進城的青澀少女隨歲月變成目光渙散的老妓女、看著火車站內找機會的盜賊。
推理小說便在生活裡尋找蛛絲馬跡,設法找出答案。
奚默農寫,當時巴黎警察兩個特徵:穿大頭靴是因為待遇低,這種鞋子耐走;留大鬍子的起源不明,但大多數年輕人加入警界就是想留大鬍子,覺得酷。讀者隨著大頭鞋同時也進入警察的日常生活,人物像在定格的畫面停留好幾分鐘,然後突然間走起路、說起話。
雷蒙.錢德勒的《大眠》,嫌犯卡門小姐到偵探社找偵探馬羅,他們之間有段對話。「幹這一行(偵探),如果你誠實的話,賺不到什麼錢。如果你有門面,那表示你賺了錢──或者準備撈一筆。」馬羅這麼介紹自己的辦公室。「噢,你誠實嗎?」卡門一邊打開皮包一邊問,她從一個法國製琺瑯盒裡取一根菸,用一只口袋型打火機點火,然後把琺瑯盒和打火機丟回皮包,任由皮包開口。馬羅回答,「誠實得很痛苦。」
馬上了解馬羅是什麼樣的偵探,了解他的日子不太寬裕,而找上門的女客戶則有錢到滴油。
以《後車廂輓歌》(Trunk Music)創造出著名偵探鮑許的麥可.康納利(Michael Connelly)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偵探的工作,不再古典時期的優雅,非常冷硬時期的寫實。鮑許談到偵探的工作:「有個雕刻家,當別人問他怎麼把一塊花岡岩變成一尊美女雕像?他說他只是剔除不屬於女人的部分。我們現在要做的也是一樣。」偵探得拿著小鑿子對花岡岩一點點的敲,不能太用力,萬一敲太多,黏不回來的。
好看的推理小說必從人性著手,一如巡邏警察偵破殺人案於他的日常、靠他的每一步,這是他的人生。一如拿破崙部下說:「皇帝打勝仗靠的不是我們的刺刀,是我們的腳。」
陳雪的《親愛的共犯》一方面女刑警周小詠追查殺死富商二子張鎮東的凶手,一方面作者追查到底「家」該如何定義?真正的家在哪裡?
為此,陳雪詳細介紹豪門張氏一家三代居於一棟低調豪宅白樓內的生活點滴,大家長張大安原想這樣能凝聚家人的感情與力量,卻忘記錢畢竟是萬惡之源。錢未必可怕,錢帶來的勢利與階級才可怕,稍稍處理不慎會帶來大禍。這三代糾葛不清的恩怨情仇便是故事的大背景。
同時,作者暗示:少了愛,這是家嗎?
另一群成長於育幼院的年輕人,他們未忘記當年以院為家培育出濃郁革命感情,彼此關照,當其中一人有難,其他人不顧一切的設法為之解脫。
作者再暗示:這樣的感情不算家嗎?
透過女刑警的不懈的偵查,她帶出一個人物串接一個人物,帶出每個人的故事,像是拿破崙手下的法國大軍,所有人物奮力的前進,抵達戰鬥位置,組成綿密的戰列,等著作者下最後的攻擊指令。
《親愛的共犯》追查的是我們究竟該認同哪一種的家。人生百分之九十處於大多數人認同的軌道上,像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在《黑暗,帶我走》(Darkness, Take My Hand)裡說的:「他們在人生中載浮載沉,如同浮在熱水上的塑膠鴨,有時會翻側到一邊,等到有人把他們扶正過來,他們又回復先前的載浮載沉。他們不吵架,也沒有真正的熱情。」
張鎮東對家人施暴,對事業、對家庭只有要求而不無付出,家裡的親人設法掩蓋事實,像把翻側的塑膠鴨扶正,他們有錢有地位,卻不知道自己失去了熱情,那麼鴨子的倒或正有何區別呢?
女警探周小詠找出凶手,然後呢?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塔斯這麼做結論:「尋找真相時,要對不可預期之事有所準備,因為真相總是如此難尋,而且總是在你尋獲時困擾著你。」
想到某本小說裡說的:
「問題不在於你能不能找到真相,而在你能承受得起真相嗎?」
本文作者
張國立
知名作家/美食、旅遊達人/擅長推理小說、歷史小說等。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曾任《時報周刊》總編輯,得過國內各大文學獎項與金鼎獎,文筆既可詼諧亦可正經,作品涵蓋文學、軍事、歷史、劇本、遊記等各類題材。近期作品:《乩童警探:偏心的死刑犯》、《炒飯狙擊手》、《金陵福 史上第二偉大的魔術師》、《海龍改改》、《一口咬掉人生》、《戰爭之外》、《鄭成功密碼》、《張大千與張學良的晚宴》、《棄業偵探:不會死的人,一直在逃亡的億萬富翁》、《棄業偵探01:沒有嘴巴的貓,拒絕脫罪的嫌疑犯》、《偷眼淚的天使》……等。小說《炒飯狙擊手》已售出北美、尼德蘭(荷蘭)等國外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