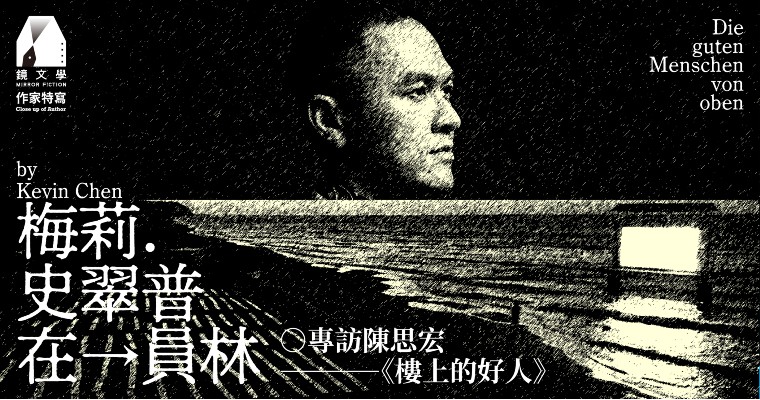
追問梅莉史翠普是不是真的在員林前,不妨先看《艾蜜莉在巴黎》。儘管這部影集毀譽參半,但陳思宏說至少有一點它寫到點上了。
「第二季有一集巴黎熱浪38度,艾蜜莉家沒冷氣,辦公室也沒,熱到快崩潰。她的法文班同學跟她說嘿我家有冷氣,她就去了,順便上了床。我看到這一幕覺得太真實了,因為柏林也會熱到38度,我朋友常常說誰家有冷氣我就要嫁給他。」
「她在熱浪中變形了。」陳思宏說。這恰恰是他用三部曲寫夏日的想法──高溫蒸汗,禮教氤氳,氣味流竄,人意識到自己與他人身體的存在,為此焦慮卻也興奮。
當遮掩的羞恥散去,慾望便成了醍醐味,引出脆弱也最真的自己。

陳思宏 著
出版日期:2022/3/4
當做戲的女人無法演活自己
細數三部曲,從永靖出發,繞道佛羅里達,最終復返員林與柏林;《鬼地方》在中元溽暑、紙灰飛揚中揭開家國大大小小的傷痕;《佛羅里達變形記》撕毀青春謳歌,正視少年少女成長痛與被迫做的美國夢。
收官之作《樓上的好人》,或許是陳思宏三部曲最貼近寫女性的一次。不同於《鬼地方》寫好幾名女性半活不死的生命史,《樓上的好人》將繁複工法用在同一名女性角色上,一針一線將她繡得立體,有聲有色。在《樓上的好人》,陳思宏把此前「夏日三部曲」的核心「變形」跟做戲結合,指出了其中的弔詭之處:為何當女性變形,變得不像原本的自己,才得以停止做戲?
陳思宏說,自己喜歡描寫女性多過於男性,「因為女性在男性掌控的社會必須變出許多面貌求生。」不由自主的女性,總是扮演他人眼中的自己,假裝開心,隱藏悲傷,否認慾望,複述男人給她們的台詞。
迫在生活中粉墨登場的女性,都活成了戲精梅莉史翠普。千千萬萬的梅莉史翠普上演不屬於自己的戲碼,「她們更引起我的興趣,也更值得書寫。」

▲《樓上的好人》是陳思宏「夏日三部曲」最終作。他稱自己有準時焦慮症,寫完浩浩蕩蕩三部曲那一刻的心情是,「很佩服自己,沒有遲交稿,甚至提早。」完成三部曲的目標,會不會覺得鬆口氣,可以慢下來了?「我不知道欸,這應該是完成人生里程碑的心情,但我覺得自己還沒做到。」他透露接下來想寫的還是三部曲,以數字為出發點。(圖/鏡文學)
一場夏日破處之旅
《樓上的好人》敘述住在員林的女主角「大姊」到柏林找小弟,經歷一連串觀光客的不適跟文化震撼,平行回望員林童年,其中藏著小弟出走他鄉的祕密。不過且慢,大姊還有一個更重要任務。她想要破處。
小說以「員林老處女來柏林了」破題,尋弟之旅成為破處之旅,《樓上的好人》因此延續從陳若曦《紙婚》、馬森《夜遊》以來台灣文學中的女性異國探險系譜。影像中也有類似的女性身影,例如茱莉亞羅勃茲演出的《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與茱莉安摩爾的《Gloria Bell》。
「在異國的月光下,我們更容易變形,因為無人知曉。當周遭都是聽不懂的語言跟陌生面孔,你就會解開束縛,因為束縛都來自人情。」陳思宏說。白話一點就是,「你看很多同志到一個新國家、地區,都是先打開交友app,尋菜一輪。」
然而,相較上述影像作品的輕鬆寫意,《樓上的好人》裡的大姊有許多磨難。首先,她並不討喜。大姊充滿怨懟,初來乍到德國,看一切都不順眼。更可怪的是,她曾是護家盟。談到大姊這角色,陳思宏有幾分猶豫(同時帶著興奮),「儘管我擔心讀者不喜歡她,但跟著她走完這夏日旅程,我相信讀者會喜歡她。」

兩則反同現場的記憶
如果在柏林,一個護家盟老處女。小說一下便有兩個惹人議論的標籤,想發文罵人的讀者,不妨先聽聽陳思宏描述的2017年同婚釋憲現場。
「婚姻平權運動多數期間我不在台灣,釋憲當天剛好我在場。那天立法院前同志聚集,彩虹旗飄逸,大家看起來都很開心,僅僅過條街,就是身穿白衣服各式不知道什麼盟的人。這帶給我很大的視覺衝擊。我在兩邊遊走,反同方有錢到有流動廁所,我注意到上面有彩虹標誌——其實是流動廁所公司的logo,就故意問,欸你們廁所貼彩虹標誌是怎麼回事,你們是支持同婚的嗎?接著,此起彼落的尖叫聲包圍我,一群白衣人對穿花襯衫的我尖叫著。其實這讓我很興奮。我默默記下這一群對我尖叫的女性。後來我把她們揉進大姊這角色。」
陳思宏說,關於婚姻平權有很多論述,「但我想知道一個來自員林的小家庭如何面對這個撕裂社會的議題,以及,一個女性為何想加入反同陣營?」
為了寫《樓上的好人》,陳思宏訪問了五位曾參與反同運動的女性。他發現她們的共通點是,其實不大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問其中一人說,你為什麼討厭同性戀?她嚇得連忙否認說沒有啊沒有。」
陳思宏的結論是,她們是寂寞的人,把教會視為家庭的延伸或補充。「對她們來說,加入教會其實像結婚,想逃避孤寂而加入群體,再被這個群體動員,做自己也不明就裡的事。」
當天稍晚,還有另一個場景令陳思宏印象深刻。「我離開立法院後,走到台北火車站,看到一個全身白衣的阿姨迷路了。迷路的她遇上一群很明顯是同志的男生,這群小gay跟她說阿姨你跟我來。於是花花綠綠的小gay領著一個白衣阿姨。我覺得這畫面超有趣,就遠遠的跟蹤他們。我不知道這件事對那個阿姨有什麼啟發或質變,但我相信她之前一定沒有真的跟同志相處過。」
這便是《樓上的好人》給出了一個不合時宜的女主角的原因。陳思宏說,「這很有趣。我寫女性都希望她們能盡最大力量違反『原廠設定』──那些對女人的期待跟枷鎖,可以不用好看,不用瘦,不用結婚,不用溫柔,不用體貼,不用當母親。我想到,啊那些對我吼、對我尖叫的反同女性豈不是正違反了這些原廠設定?」
老處女礙著了誰?
《樓上的好人》主角除了是現實中曾對陳思宏尖叫怒吼的天選casting,還動用了他讀彰中的老處女記憶,「我一直都對老處女這稱號很有興趣,這稱號有個衝突,老了卻還是處子之身。我們在各種語言中都可以找到相應的詞,因為各種文化都常常以性貶抑女性,用性來判斷一個人值不值得存在。」
但老處女礙到了誰?「從小到大,學校裡都有一位被稱為老處女的老師,我讀彰化高中時就有一位。同學們用各種方式羞辱她,例如全班忽然大笑,在她經過時大叫老處女。」
「求學階段我跟這些被稱為老處女的老師都很好。她們發現了我的不一樣,在群體中處於弱的一方。或許,她們在我身上也看見了自己的影子。」因此,在冒犯的風險下,陳思宏書寫這樣不合時宜的女性,讓角色作為證明般的存在。
證明女性可以不用是社會給的原廠設定。證明男人不能用自己狹隘的目光,囚禁活生生的女性。證明自己曾經在求學路上遇到雪中送炭的隊友。

一個男同志寫反同保守女性,是有趣的跨界,但是不是也是冒犯呢?我刻意問陳思宏。他的回答是,「寫作就是關於跨界,如果只能寫身分規範內的,那我們寫小說幹嘛?確定自己基於尊重,就不要怕冒犯別人,要找到一個溫柔的施力點,建立對話的可能。」
不過小說既以老處女想破處推動故事,最後勢必要寫到她究竟能不能如願。「這是個難題。」陳思宏說。因為寫多一不小心就會俗套,甚至重回陳思宏所謂的「原廠設定」;寫少,則又會讓讀者有隔靴搔癢的感覺。
「身體被綁住的女生,被打開了,她會怎麼辦?」陳思宏構想大姊的破處。「我覺得大姊的性會是帶荒謬的喜感。我不想寫光彩的性,這關乎我們對性的期待想像,以為總是光鮮亮麗,一定要俊男美女香撲撲乾乾淨淨的,然而實際上不是這樣。有過性的探索就知道,跟人生一樣,大部分都是失敗的。」
因此,小說最後大姊對她的破處對象說:「我不美,但你可不可以專心看著我。」用獨一無二結合員林與柏林的方式達致了她的願望。
小說這樣描述:「原來這就是性。等一下,這就是性嗎?身體幾秒連結,進入,往前後退,癱軟鬆垮,好累喔,懶得遮掩,不用裝美,不想收肚,我不介意你的疤,你不在乎我的老朽。他放了個屁,微臭。她聞著屁,感到前所未有的鬆弛。沒人需要為了屁聲道歉,沒人需要為了鬆垮道歉。」
這是最不浪漫同時最富人生況味的性了。
三部曲終章:陳思宏的影像之書
等一下,所以梅莉史翠普只是一個浮想聯翩的比喻,不曾踏足員林?不,她真的來過,在小說的最高潮,陳思宏動用了小說家無以倫比的連結時空跟情感能力,讓梅莉史翠普以她拿下首座奧斯卡女主角獎的《蘇菲亞的選擇》在員林重現。
「我一直想把梅莉史翠普寫進小說裡。追根究柢,我就是一個死文青,喜歡把看過聽過,然後有感的影像音樂放到故事。」從《蘇菲亞的選擇》到《新天堂樂園》,從曾屹立員林的國際戲院,到柏林如今還開張的「國際電影院」(Kino International),都被陳思宏寫進《樓上的好人》。
用一本小說連結複數的電影文本,讓不同作者展開對話,相異的地域交疊。於是梅莉史翠普「成為」《樓上的好人》角色,員林與柏林互為前世今生。這關乎陳思宏對進電影院看電影的由衷好奇。「我常常想為何人類喜歡看電影?因為燈關了,在黑暗中我們是被帶進另一個宇宙,這是串流無法比擬的。美國有陣子盛行歌舞片,因為蕭條年代需要娛樂,進入電影院,就是進入萬花筒;跟歐洲不同,歐洲是到電影院逼你面對現實。我們在電影院共享一個私密的宇宙,不論是逃脫還是面對現實的電影,都是小說可以施力、拿來取用的。」
因此,《樓上的好人》是陳思宏的影像之書。小說裡,唯有當大姊與小弟在電影院,他們才真正回到了故鄉,那裡有他們共同的快樂記憶。至於陳思宏自己,「我想透過小說說一次我愛電影院。」
存在與不存在員林的梅莉史翠普,以及小說接合電影文本,在在顯示作家調度想像與挪移現實的本事。陳思宏說,「有人不喜歡談論小說設計,但我覺得設計是很重要的,我很高興看到很多寫作者一起回到虛構跟想像的力量,帶我們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寫完三部曲,陳思宏對自己的期許是「一個無聊的說書人,但把想像力放到最大」。夏天三部曲完結了,但夏的記憶不會散去,我們跟著主角不可免的袒露自己,其實就是認真看一看不成人樣的自己。
三部曲最終的提問或許是,你怎麼知道那個不成人樣的自己,會不會其實是真實的自己?變形,其實是變回。陳思宏在三部小說裡寫出的夏日奇觀,不過是人們初來世界,最柔軟無所畏懼的一面。
小說家用夏天的故事訴說被壓抑的曾經。

▲陳思宏把梅莉史翠普寫進了《樓上的好人》。當年他曾在員林國際戲院看她演的《蘇菲亞的選擇》,而柏林也有一個「國際電影院」。因此,電影或者說電影院像小說裡的蟲洞,打通了過去的員林與現在的柏林,年幼的大姊與小弟探頭看見此刻已疲憊不堪的自己。圖為柏林國際電影院。(圖/陳思宏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