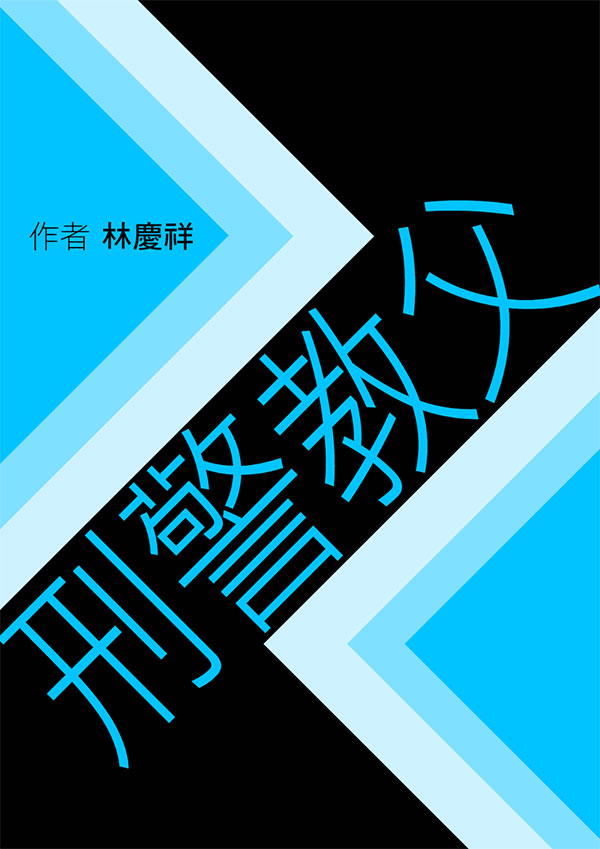「小弟是妳的,伊是恁張簡家的孤子,對志雄來說,伊小弟幾百個,不差這一個,阿瑞仔也不是會幫公司賺錢的幹部,講卡歹聽,恁小弟生雞蛋的無,放雞屎的有,減一個沒差,飼太多擱呷了米。若對我來說,偷偷放小瑞走,是犯法的,會害我嘸頭路,妳隨便到警政署檢舉,我就下課了,尚蓋好是恁小弟乎黑道的殺手打死,嘿嘿!攏無證據,我就安全了,但為何我要告訴你這些?因為人是有感情的,要講義氣,我陳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則,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氣魄,我嘛不輸他,阮攏是愛伊好、驚伊死」。
他最後再補一記回馬槍:「阿妹仔,我今天跟你講的話,妳去跟志雄講嘛嘸要緊,但是,未來的代誌安怎變化,無人知道,我勸妳對任何人攏要有所保留,聽聽就好,對我、對志雄攏仝款(同樣),妳尚好連我嘛莫全部相信,妳自己判斷,但別忘了,如果妳覺得需要我這個老大的時陣,可以來找我,我是警察,有法律約束跟立場,我不是流氓,不需要靠殺手恐嚇擄肉(綁票)來賺錢」。
短短兩段敘述,或可稍稍拼湊出故事的樣貌:對話者一男一女,女方的弟弟小瑞是黑道老大志雄的小弟;發話的男方是個刑警,在此無法判斷官階,主要目標是小瑞;而女方因弟弟的關係成了夾心餅,誰都信,也誰都不信。
這只是林慶祥首部長篇小說《刑警教父》中的一個場景,但已足夠讓人嗅到這部小說當中的氣味:警察、黑道、江湖、義氣、勾心鬥角、爾虞我詐,與不得已。
沒有英雄的世界
林慶祥的小說裡沒有俊男美女。他筆下的警察們,沒有誰是可以一次打十個的不死英雄,也沒有出入槍林彈雨還能一臉痞樣談笑風生的最佳男主角。在《刑警教父》裡,無論是警界的刑事小隊長陳江、黑道大亨陳志雄,或是雙方因著不同目的共同鎖定的頭號槍擊要犯小瑞,沒有一個是英挺偉岸的角色(在聊到若作品改拍成影視劇該由誰來演出時,林慶祥針對小瑞一角還特別強調:不能是帥哥)。卻也因此,書中情節的種種描述,都不再是螢幕/銀幕那端的雲端想像, 而是拳拳到肉、黑白兩道的血淋淋人生。在當代為數不多的台灣犯罪小說中,《刑警教父》的出現,無疑為社會寫實路數的類型作品添了一枚生力軍。
而是拳拳到肉、黑白兩道的血淋淋人生。在當代為數不多的台灣犯罪小說中,《刑警教父》的出現,無疑為社會寫實路數的類型作品添了一枚生力軍。
警政線跑了十多年的林慶祥,說老還不至於,但早也累積了一大資料庫的故事等著倒出。「我想寫這部小說想了很多年。應該說,從我知道這些事,就一直想把它寫成小說。」搖筆桿的人,多半抱著寫小說的夢,何以拖沓到年近半百才以新人之姿出道?「年輕時有很多時間可以寫。那時還沒結婚,那個年代在日報工作,壓力也不像現在這麼大。但說真的,那個年紀,寫小說哪有比去酒店喝酒、比跟黑道、業者、警察混在一起好玩?怎麼可能下班乖乖回家寫小說?當然是朋友喊了就走啊。」林慶祥說話豪爽,直率且坦白,「尤其那時警紀風氣很差,我只要打三通電話,一定會有人正在酒店喝酒,叫你趕快過去。你還會回家寫小說嗎?時間就這樣蹉跎了。」
 在高雄市政府任職,每天與媒體打交道,與記者兄弟聚餐,那時喝酒也比寫小說重要。
在高雄市政府任職,每天與媒體打交道,與記者兄弟聚餐,那時喝酒也比寫小說重要。
初入行的記者,人脈重於文筆,「剛開始忙著建立自己的名聲,擔心認識的人不夠多。」記者最計較自己的聯絡資源夠不夠廣,遇到刑案知不知道要問誰、能不能問到對的人?為什麼別人問得到自己問不到?為什麼這個分局的隊長會把訊息透露給誰,就是不告訴你?凡此種種,都關係著記者生涯的光明順暢與否。「所以你會把很多心力花在這裡,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也是自己愛玩。」畢竟沒有人就沒有線、沒有來源。「所以年輕時的確過得比較……紙醉金迷吧。」他乾笑,流露出一點尷尬。「但寫小說的念頭一直在,午夜夢迴時會很愧對,幹,自己怎麼這麼不認真、這麼鬼混。也想過要先寫點短篇小說,但都沒想到什麼好的idea……」講沒兩句他又大手一揮:「啊其實都只是想想而已啦,還不就是懶。」他放棄替自己洗白了。
不看好也要完成
2011年前後,林慶祥幫高雄市長陳菊打完選戰後離開市府。「當時在家連續糜爛了好多天,每天都跑出去喝酒。突然某天一個念頭闖進來:幹,我如果再不寫,這輩子永遠都不會動手了。於是電腦打開,想了開頭,就寫了。」他頓了一下,不無擔心地問了一句:「所以開頭很弱喔?」
還來不及回答他弱或不弱,他又喃喃地自白,「寫到一半時無以為繼,不知道怎麼寫,中間停了好久。寫到後來甚至會覺得:它值得寫嗎?我寫得完嗎?這麼爛,值得再寫下去嗎?」每一章寫罷,林慶祥都沒有多邁進一步的喜悅,而是從自己的寫作能力到技巧,各種自我質疑反覆不斷。「一直到後半我才有點自信要把它寫完。」但不是終於認為自己寫得好,「那時想的是:即使真的很爛,總也要把一件事情完成。」是這樣的信念推著《刑警教父》走向結局。「我自己從頭到尾都沒有很看好它。」他說。
 每一個想動筆寫小說的人,心裡一定有你關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關心的。
每一個想動筆寫小說的人,心裡一定有你關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關心的。
「會寫不下去的另一個原因是,最初我只有隱約的想法和人物,沒有先想好大綱,也沒有結局,那種『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的情況真的很痛苦。而且我太耽溺於自己對警界生態的瞭解,光是開頭的監聽我就寫了一大堆。這都不是好事。」對自己寫作上的缺失,林慶祥看得比誰都清楚;而「第二本一定要把大綱都弄好再動筆」這句話,在整場訪談中大概出現了八百次,足見這種「邊演邊生劇本」是多麼折磨。
善惡無關黑白
然也因為林慶祥對警界生態的瞭若指掌,讓《刑警教父》擁有難以摧折的堅實骨架。他在台灣警紀風氣由濁轉清的關鍵時期進入新聞圈,那段警察比黑道還囂張的年代,他雖未能躬逢其盛,卻也耳聞不少。警政新聞的長期磨練,讓他懂得什麼時候可以適當探究,什麼時候可以硬起來翻桌;什麼時候該放軟打聲招呼,而什麼時候該閉上嘴。這些都滲入了小說裡,成了血肉。「寫警察,這是我最熟悉的題材,我和這些人也是有感情的。」
「我對警察很熟,一直想寫的也是警察的故事。每一個想動筆寫小說的人,心裡一定有你關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關心的。」
在林慶祥的小說裡,無論是遊走黑白兩道的刑事小隊長陳江、試圖金盆洗手的黑道老大陳志雄,或亡命天涯的小瑞,都有雙手染血的時分,也有顯露人性光輝的瞬間。「這部小說裡幾乎沒有好人,也沒有誰是真正的壞人。只有三個想回家的人。」陳江想安全下莊退休養老,志雄想海撈一筆拍拍屁股走人,小瑞想回到故鄉侍奉雙親。他們各懷鬼胎,也各有心軟。黑道不全為惡,警察更不是永遠的正義代表。在林慶祥所認識的警察中,不乏陳江這樣一手犯著某些惡行,轉過身面對本業又兢兢業業者。「貪汙索賄、智勇雙全,都可能並存在同一個人身上。很多英勇殉職的警察也是很黑啊,平常違法的事情一件都沒少幹過,碰上要拚命的時候,熱血一沸騰也是往前衝。所以你要怎麼論定一個人?」
所以又回到陳江對小瑞胞姊講的話:「……人是有感情的,要講義氣,我陳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則,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氣魄,我嘛不輸他,阮攏是愛伊好、驚伊死」。置身白道,卻與黑道相互比擬、爭一口氣,刑事教父比誰都要更懂得翻雲覆雨;善惡之間,或許連一線之隔,都稱不上。
資深記者談記者:關於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
 年輕時的他,在馬祖服役留影,當年為了放假回台灣,寫違心之論的小說,還真的放了兩航次的返台假。
年輕時的他,在馬祖服役留影,當年為了放假回台灣,寫違心之論的小說,還真的放了兩航次的返台假。
在和林慶祥聊他的工作經歷時,他先講結論:
「我這輩子只幹過兩個工作,一個就是記者,一個就是應付記者的人。」
林慶祥是宜蘭孩子。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覺得在家鄉不好求職,就跑到台北找工作,找了兩個月還是沒著落。某天一個朋友邀他到台中家裡喝酒過夜,次日一早兩人買了份報紙坐到麥當勞看台中的地方徵才廣告,發現有家《震撼》雜誌在徵記者,就去了,自此踏上新聞路。「我從沒想過要當記者,一生隨波逐流。」他笑。
從泡茶聊天到公事公辦
在《震撼》雜誌待了一個多月,老闆跑了;1996年年底輾轉到彼時剛復刊的《台灣日報》,從環保、區里新聞開始跑,之後轉到警政線,一待近10年,累積了他絕大多數的資源與人脈。2006年《台灣日報》收山後,他到《民眾日報》沾了一下,隨後進入公部門任職,成為他口中的「應付記者的人」。過幾年撤出公部門,重新披上記者戰袍,回到新聞現場。
20年前當記者,和現在幾乎是完全不同的生態。「小時候多可憐啊,(為了新聞)每天晚上都要去陪警察泡茶,還帶宵夜去請他們吃,坐到三更半夜。」警政線的記者與警察關係亦敵亦友,有親密換帖的時刻,也很容易因立場相對而起衝突。和警察日夜「搏諾」(台語,意指建立交情),不只是為了不知哪天會到來的大新聞做準備,更是彼此之間的信任感。「當然我們和警察還是會互譙:『幹,條子都靠不住』、『媽的,這些記者,說變臉就變臉』,但信任感都還是在。」然現在的年輕記者與警察,大家都成了行禮如儀的上班族,少了互動,也省了獨家。一切都由秘書室發新聞稿,或用LINE發群組。公事公辦,不需攀附談交情,但也缺了衝激的火花。
「現在的記者,坦白說,比較沒有實力。想(用報導)修理人,也不知道從何下筆,修理不到痛處,人家也不會怕你。這個社會很現實,很多東西都是交換來的,你有實力人家就會尊重你。警察也是。」
即時當道,技藝不再
 伏案桌前,以十五年來與警察朝夕相處的經驗,寫下精采絕倫的《刑警教父》
伏案桌前,以十五年來與警察朝夕相處的經驗,寫下精采絕倫的《刑警教父》
所以現在記者比較好當嗎?「難。」林慶祥簡單吐出一個字。老鳥如他,也同樣面臨著即時新聞的壓力。「現在報社重視即時,比重視一般新聞更甚,很多新聞專業就這樣被犧牲掉了。」已經不是先求有再求好,而是有了就好。「你不能否認新聞它是一門技藝。從題目為何產生、怎麼寫、怎麼瞭解事情的輪廓、怎麼表現,都是技藝所在。」但現在這門技藝的原則和工法,為了搶時效、充版面,往往被迫省略。「就像做鞋。一雙好的鞋,該怎麼縫、該縫幾針,要做到才穿得耐久。假如隨便縫一縫,只求有個鞋樣,當然穿不到幾天就壞了。」林慶祥搖搖頭,噴出一口煙,不知是替年輕同業嘆息,還是替自己。
說起鄉民最常嘲弄的那句話「少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林慶祥還是搖頭。「記者這個行業,入行門檻很低,而且是愈來愈低。但無論時代怎麼變,要當個好的記者,永遠是那麼難。」感覺上這個職業一直被貶低,「但你會發現,社會上有三種人,只要一提起,大家都沒好話,可是一出事,又很希望自己有這樣的朋友,就是民代、警察、記者。為什麼?因為這三種人有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簡單幾句,帶出記者令人又愛又恨的原罪。林慶祥把手上的菸彈熄,不再多說。再問他,那怎樣是好記者?他沉默好半晌。
「沒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