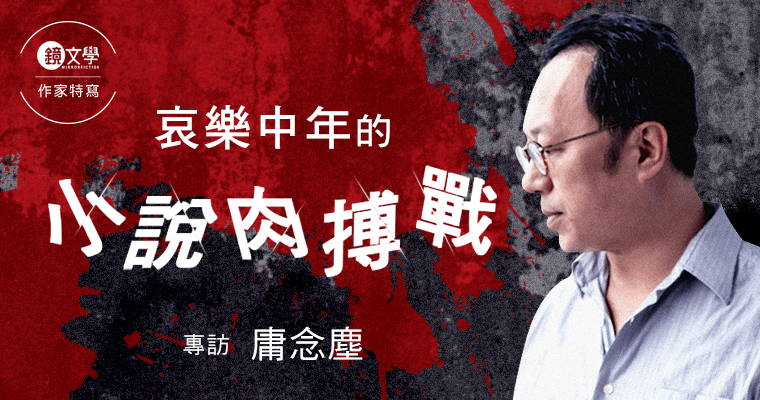
【作家特寫】哀樂中年的小說肉搏戰——專訪庸念塵
+ More 立刻閱讀:《Quarte》庸念塵說話給人過分小心翼翼的感覺,回答問題像傾訴秘密,會先看看四周,再下意識用手遮掩——與他說出口,其實很平常的內容顯得反差。在謹小慎微的背後,庸念塵說他最愛的電影都是韓國片,例如奉俊昊,用血性直取社會病灶。創作者與滋養他的社會,往往互看不順眼,奉俊昊是一例,庸念塵也是一例。庸念塵的文字相當簡練,這樣的寫作風格並非偶然,他曾任日文翻譯,役畢後赴日求學,返臺後在日商公司工作,翻譯半導體相關文件,現專職寫作。不同於我的成見——接觸翻譯會干擾創作語言的「純淨」,庸念塵認為翻譯專業術語文件是種訓練,幫助他自由跳躍在中文與日文語法間。「從日文翻譯成中文,不只字數會急遽減少,還要懂得斷句,對語氣的掌握得更到位。」翻譯之於庸念塵,宛如搬弄各種詞性的方塊,是練習「把一個字擺在它該在的位置上」的過程。少年情懷質變問及最早的文學接觸,庸念塵坦言一開始是為了追女孩子。少男情懷驅使他抄寫泰戈爾的詩到情書裡,後來索性不抄了,自己開始寫,一頭栽進文學海裡,游來游去又闖進小說世界,一路寫到現在。現實與期待的落差,往往造就一顆敏感的心,庸念塵自言:「從小就樂觀,但多愁善感。」他的童年在新竹關西的客家庄度過,直到六歲父親過世,母親舉家搬到士林,「大人說隔三座山就能到關西,於是我天天坐在陽台望著遠方。」過年於童年的他,是淒風苦雨的路途。在寒冬中遙赴新竹,大家族熱鬧一輪後,再次回到沒有同伴的台北生活。這種匱乏與完滿的對比,就好比他在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獲獎之作《血漢橋》裡寫的孤兒寡母——甘伶與忘仇,從相依為命到豁達人生,看似以淡然鑄成遺忘,內心卻如潮湧不止。小牢騷撞出大宇宙談起自身寫作的意義,庸念塵說自己是凡人,不免有挫折,創作是他唯一能發洩的管道。因此,生活小事被放大擴寫,長成一片有機的小說世界。「老實說我是對這世界有所不滿才寫的。」小至在早餐店前遇到機車亂停擋路,大致目睹酒駕虐嬰在媒體上不斷放送,滿腹牢騷撞出文學宇宙,委屈一筆入魂。用寫作宣洩已是習慣,庸念塵說他出社會後,對世界有更多不平衡的不滿,「大家都說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可是最醜陋的也是人。」憤慨即使有當頭棒喝的力道,仍必須用藝術呈現,否則便與酸民無異。轉身至小說家,其責任便在揭穿虛偽。「我覺得臺灣可以更好。」庸念塵說。換個角度看,以武俠起家的庸念塵也是見惡行義。本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語境不復存在,英雄豪傑的不平之鳴已隨亂世而去,取而代之的是承平時代裡抒情的牢騷。即使庸念塵寫武俠,他早早立誓不作金庸傳人,「金庸只有一個,再怎麼寫也無法超越他,以他的套路寫下去沒有太大意義。」於是,庸念塵鎖定清末民初的鏢局與氣功,仔細鑽研成現代武俠《血漢橋》、《兩聲雷》,抓準京片子語言揉進敘事,用真實的社會制度與武術作框架,寫下不凡的人事。要言之,這是以說書口吻拳拳到肉的考究作品,尤其鏢局的炮捶拳或氣功都是真正的武術。原來庸念塵練過半年的詠春拳,便將興趣與寫作結合。於是不平的平凡人揮拳,赫然劈開小說路。與怪現狀肉搏「比起單純的運動競技,擊劍更傾向武術。」庸念塵說。庸念塵動用十九萬字鋪寫《Quarte》(四分位),是臺灣少見以擊劍為主題的長篇小說。《Quarte》以擊劍教練池顯龍遭擊劍高手以四分位(擊劍運動的有效攻擊部位分為八,四分位接近心臟位置)刺死作為開場,用駭人情節與推理懸疑手法,鋪展出一段段因擊劍而生的人物因果,並投射對臺灣擊劍與社會現況的反思。說起擊劍,庸念塵真的肚腹有經:「擊劍相當公平,沒有辦法靠運氣。選手在直線、有限的空間移動,為了在短時間內判斷得分位置,每個動作都必須冷靜且精準,所以技藝精湛的擊劍選手往往文武雙全。」原來庸念塵有個曾是擊劍國手的叔叔,自己赴日後也學起擊劍,日後更將兒子拉到擊劍的領域。然而,越是深入越是湧現無數的怪現狀,「有的家長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讓小孩練劍,也有教練會故意留一手,因為他底下的學生有人比較有錢,『那一手』要留給錢付比較多的。」小小擊劍界儼然臺灣光怪陸離縮影,怪獸家長與不道德的教練,在在令庸念塵受到極大刺激,整部小說於是有了寫實基底。庸念塵的文學初衷來自少年情懷「為了追女孩子」,如今寫的卻多是推理與武俠。新作《Quarte》以一樁命案劍指臺灣運動界怪象。寫作於他越來越像擊劍,只能選擇攻擊,或思考如何防守——等待下一次攻擊機會的到來。值得一提的是,《Quarte》設定時空背景在2030年代,文明應當因科技發展而躍進,小說人物卻回到更原始的肉搏戰——在地下鬥劍場卸下裝備與電子儀器,將仇恨以血肉作為清償的工具。「誰說未來一定會更好?人性可能更野蠻、更血性。」庸念塵說。這時,他彷彿展現了黑暗面,類似奉俊昊電影的那種。《Quarte》也反思傳播方式與暴力的糾葛——小說人物以「直播」帶動人們暴力的欲望,庸念塵進一步點出現今自媒體的矛盾:「自媒體本該是個人化的表彰,最後為了譁眾取寵而集體平庸了。」點擊率至上的時代來臨,跟風使世界變得單一。問他也看直播?他說自己會跟兒子一起看「館長」。擊劍作為小說的引子,事實上要揭穿的現世裹在內核。庸念塵說:「《Quarte》設定在近未來,不僅是對當下的批判,更是提醒:我們要的是什麼樣的未來?」當抄著泰戈爾的文藝青年成為過去,血氣方剛或許不再,但庸念塵對黑暗的人性施以血償的文字技藝,宛若擊劍在直線前進的空間裡一對一對決。「擊劍是無法遁逃的運動,你只能選擇防守或攻擊。」庸念塵執起他的筆向我說道。

【作家特寫】劈出眾宇宙 小說家明善的腦洞大開之路
+ More 立即閱讀:《迷霧森林》本職是科技業主管的明善,說起話來有條不紊,彷彿在腦中沙盤推演許久。說話,不過是他讀取思緒的過程。寫作亦如是。半路出家寫小說不過兩年的他,已完成五部長篇若干短篇,以及正在連載的《穿越異世界不是你想像中這麼簡單好嗎》。追索他的創作之路,我們可以看到一位主知且多變的小說家正慢慢浮現。複系統的人生與寫作初見明善前閱讀一大落資料,心底湧起滿腹疑問。到底要怎麼同時一手寫一大套武俠,一手寫輕小說?本業是矽谷在台科技業的主管的他,又是如何走上寫作的「不歸路」?翻讀稿件時,我以為他會是很跳的不世之人,不然怎會將「氣三部曲」從武俠寫到了科幻;看到他身為科技主管的資歷,腦中又浮現正經八百的西裝大叔模樣。直到明善真的走到眼前,腦子裡假想過的畫面統統被他一手揮掉。和諧的衝突,是我能想到的最好解釋。明善的第一印象予人老成之感,很難想像他嗜讀輕小說,愛聽日本動畫主題曲,甚至用手機「打出」一部長篇小說。看似矛盾對立又自然並存的現象,便是明善最特殊的地方。他雖然號稱「生性不安分」,卻也每天起床上班前會在書桌規律寫字,一天就能產出數千甚至數萬字。更「科技」一點的形容,或許是「複系統」。他有兩台筆電,一台用來工作,另一台用來寫作。一如他同時創造龐大的武俠世界與腦洞大開的輕小說。世界彷彿被明善切得很乾淨。或許「半路出家」亦是這麼回事。從建築系跳到資訊業,最後兩腳跨向從小熱愛的寫作;跨域從未止息,你無法確定他下個方向會往哪走去。明善的寫作肇因,源自2016年始感受到科技開發的刺激感衰退,「那時我在捷運文湖線上,開始用手機寫起第一部當代武俠長篇小說」,那便是《氣》的誕生──用一只手機敲出一部長篇,聽來像修行像折磨,明善卻甘之如飴。如何在庸碌生活中找到一個縫隙跳進去,並且在其中優游享受,明善是箇中好手。時時刻刻鍛鍊底氣的跨域者踏回寫作之路,像不知不覺中修煉出數十年內功的習武之人,一出手便震天價響。「懂得氣的人,時時刻刻都在下意識運氣。」這句他在《氣》裡的宣言,大抵也是自況。武俠啟蒙自被禁的金庸談起武俠淵源,要從初二在租書店借來的沒有封面的武俠小說講起。要到很後來,明善才知道自己看的是金庸的《倚天屠龍記》──因為那時金庸在臺灣被禁,只能暗度陳倉。然而,隨著戒嚴落幕,明善認為武俠似乎也逐漸沒落,「那時候什麼都不能寫,武俠算是那時候的桃花源或烏托邦。」解嚴後眾聲喧嘩,武俠不再是人們面對世界唯一的想像突破口。因著特殊年代的滋養,中國古典的山水園林成了明善最初的寫作素材,「我高二開始練習寫武俠,設計故事場景,誤打誤撞才發現一件事:原來我看得懂空間平面圖!」他笑著說,或許如此才闖入了建築系。隨時代變遷,武俠精神也得重新演繹。這也造就「氣三部曲」的不同面向:從《氣》對善惡的討論,到《死亡境界》藉死後去處探討人與靈的存在,最後再透過《人後》追問出空間與次元的意義。武俠在明善筆下有了歧異,跟以往正氣凜然的江湖豪傑截然不同,更多是現代時而中二還動不動吐槽的平凡人,他們觸及的世界卻因此更為寬廣,甚至可以直達生死宇宙。明善心中的「武」與「俠」為何?他非得先繞好幾個圈子才告訴我答案;那顯然是抗拒「便宜行事」的態度,非要細細推敲才落筆。就像明善告訴我,在他眼底,「武」只是手段,「俠」也只做自己覺得「正確的事」──儘管那不一定走在正道上,甚或與常人的認知有衝突,卻是他們衡量世界的尺度。或許明善也是這樣,他走在別人也走的路,可是卻非得岔出去,非得不斷嘗試。在寫作路上,明善願意繞更長的路,把自己的道理說給更多人聽,儘管所謂的道理可能是腦洞大開來的。他在紛擾的世界裡扮演自己的武俠。不走正道的創作路那麼,明善繞過什麼路?他說喜歡挑戰沒試過的東西,「因為我就是不務正業啊!」話說如此,明善的表情可是超級淡定,「寫作對我而言才剛開始,我不會寫一樣的東西,直到我抓到自己的路。」這樣的宣示揭曉他風格多樣的原因,我腦中浮現他對樁練拳的身影,像葉問,逐漸打出自己的那一套詠春。「我總是看著我腦中的『電影』寫東西。」明善這樣描述他的寫作過程。比如輕小說他也嘗試過,洋洋灑灑寫下十三萬字的《穿越異世界這種中二情節不是真的好嗎》。然而他坦承:「只有標題是輕小說,內容並不輕,無論是故事劇情或情感深度,都讓人很難輕鬆起來。」從內觀式、探討天人之際的武俠到取名就很中二的輕小說,看似很跳,對他而言卻是尋常轉換。他說他上班無聊,下班回家就看二次元動漫,輕小說也抓來啃,例如《魔女的槍尖》是他最近讀過最好的輕小說。另一套武俠他也走過。短篇集《宋筵傳》是明善「側描武俠」的方式,「這個寫作有沒有辦法達成目標,我還不知道。」他透過描繪市井小民,把武林縮為一個又一個小人物的生活,逐步勾勒所謂的武俠是怎麼呈現的。他在《宋筵傳》這樣描述小人物在俠義世界裡生存的方式:「錢小六看著滿地屍首,血漫遍野,蹲在廚下不敢動彈。心中猶豫著該去取金私藏呢,還是留金作為贓證,趕緊奔至縣衙首告才是。想了半晌,才待站起,兩腳痠麻,又朝著金錠跪了下去。」明善很清楚這些路沒有白走,因為試過了才知道極限在哪,可以決定是否要繼續下去,或者轉彎或者迴返。「我總是看著我腦中的『電影』寫東西。」明善把五官裡的空間與視覺開到最強,不斷用文字進行輸入與輸出,這就是他的文本世界,也是他的寫作足跡。寫著寫著,也就成了一條路。寫作展現腦內小宇宙雖然號稱「生性不安分」,但他每天起床上班前會在書桌規律寫字,一天就能產出數千甚至數萬字。寫作之於他,是修練,也是具象化腦內的小宇宙。訪問過程中,他看起來總沉著冷靜。我坐在明善對面,聽他說起他的創作論,總想著他在這些對話過程中又思考了什麼。明善說,舉凡新聞報導或日常對話,都是他運用的寫作素材。一個龐雜的、奇想的說故事的人就這樣跳了出來。例如他寫《迷霧森林》運用科技業背景,具象化「金鑰加密技術」,打造如《全面啟動》層層關卡的小說世界──一個封閉又滿布謎團的度假村;異色之作《慾望拼圖》用不同的人物視角拚湊慾望的凹凸有致,寫超乎常理的悖德家庭,丈夫覬覦妻子的前夫,妻子垂涎來家作客的女子,女子又愛上妻子的現任丈夫,他們正值青春期的兒子也來參一腳……腦內如斯運作的明善每天早上坐在書桌前敲打文字,一年就產出數十萬字。從事這麼文靜的活,明善卻一邊聽激昂、節奏很快的日本動漫歌。書寫,在他實踐之下,是把生活活成了一場場無聲的戰鬥。這是明善一個人打造的眾武林;男子運氣,大手一劈,闢開無數時空,朝未來筆直走去。
客服時間:週一 ~ 週五10:00 - 18:00(國定假日除外)
客服電話:02-6633-3529
客服信箱:mf.service@mirrorfiction.com
© 2025 鏡文學 Mirror Fic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鏡文學 App
好故事從這裡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