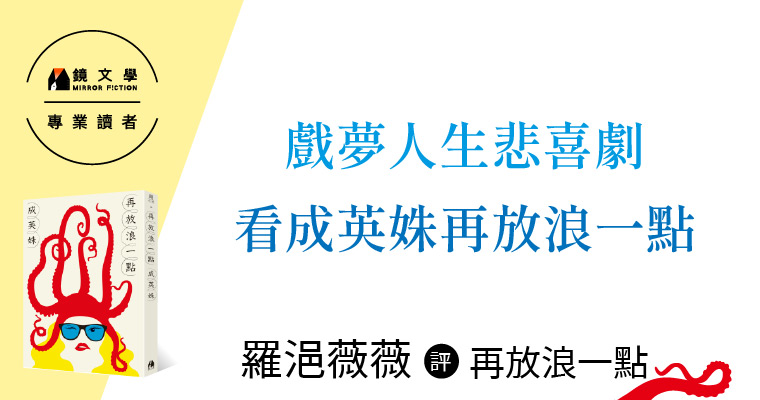
戲夢人生悲喜劇——羅浥薇薇看成英姝《再放浪一點》
+ More 我有一群不三不四的朋友,在臉書上開了個名為「D級俱樂部」的私人群組,裡頭有大學教授、家庭主婦、烘豆師、海外遊子、動畫師、無業遊民、藝術家等等共計十一人。這是個第一時間很難令人理解的神秘組合,但裡頭或積極或潛水、身懷各自武功門派的成員,加上版面裡每日的插科打諢與世界奇聞轉帖,讓這俱樂部從一開始的無心插柳到而今的藤漫成牆,人人皆從自甘低級的嘲諷底下尋出最小眾的樂子,並深深相信彼此必定能理解其中暗語。《再放浪一點》成英姝著出版日期:2020/6/12看了《再放浪一點》,我一直在想自己的D級俱樂部,認真思索著此類秘密結社之必要。說秘密,其實這並非一開始便得說出口的要件(畢竟說得出口的就不叫做秘密了),而是一種氣味,加上(聽起來無比老套的)緣分。於是我們得到了愛莫、梁夢汝、鞏麗蓮、由果,四個陰錯陽差、既排拒又親暱的角色,成英姝描摹人物,尤其女性,真是一絕,相較起她眼底各形各色環肥燕瘦的都會女子,所有的男性都成了配角。她擅於運用活靈活現的人物及情節帶動故事的節奏感,那些對話尤其簡練精彩,你完全可以想像它被改編成舞台劇:「我小時候好嚮往院子有游泳池的房子,我心想,得多有錢的人家才擁有游泳池啊?」由果說。「人總是會嚮往沒有用的東西,要游泳池到運動中心就好了,買月票才1500,不限次數。你知道養一個游泳池要花多少錢?還沒有跑車實際。」鞏麗蓮說。「你都到公立運動中心游泳?」我問。「當然不!我是女明星,給人認出來怎麼是好?」鞏麗蓮說。「她都去那種養生游泳池,有三溫暖和草藥浴的,草藥池裡頭還放薑,老人都去那兒。」梁夢汝說。由果的天真爛漫、愛莫的追問者性格、鞏麗蓮與梁夢汝的看來互相吐槽實則交心至深,四個人從面部表情到人生觀,在這個場景輕描淡寫的幾句話之中便生動描摹出來。成英姝筆下的都會女性,所需面對最波濤洶湧的,已並非社會架構底下的客觀性別困境,更多是直面規範之後自我與他者的對話,而這個「自我」與「他者」在《再放浪一點》裡,實為一體兩面、無法分割。愛莫在看待與書寫身邊各色女子的同時,看似客觀辛辣自有想法,但深究之後我們會發覺,所有的想法之中都包含著她對自身、人際、乃至於整個社會的的主觀想像。作為一個說故事的人,如同《傷心咖啡店之歌》裡頭的馬蒂,成英姝在故事裡藉主角的囈語,像在鏡子屋那樣撫著鏡中的自己,一面自問自答、苦於毫無出路,一面仍捨棄不了內心深處對於(儘管可能永遠走不到的)洞穴盡頭那絲光亮的一抹想像:「人的一生說了數不清的故事,這些無窮的故事散亂,充滿矛盾、歧義,它們會被什麼指向一處,變成同一個故事呢?」「……,但事實上,每個故事在當下便已完成了,每一個瞬間就涵蓋了過去和未來的可能,在那個點上,它已經是完整的了,有它自己的內在邏輯。人或可以眷戀、頻頻回首、躊躇未知,但活著這件事只發生、結束在當下片刻,不仰賴倒帶或者不確定的未來,因為它自己就是過去與未來。」四個個性迥異的女人們在鋪陳了大半篇章後,終於拋開俗世種種、真正地乘著噴射機離去,在旖旎南國共處一室。你若曾經計劃這樣的旅行過,便能理解最理想的旅伴不是愛人,也不好是與你太過相似的人,這有點難解釋,大致就像小說裡四位女主角那樣,可以瘋癲可以拌嘴可以完全接住你,但絕不輕易把「包容」說出口。在異鄉的放大鏡之下,你會發現自己的開放性與想像力都水漲船高,角色性格與故事走向至此漸漸收攏而愈見清晰,那就算快被現實磨損殆盡也難全然捨棄的溫柔慈悲由此淡淡浮現。我是從曉天與晴恩的支線看見那溫柔的。相較起小說中其他人物之間的關係與對話,這段故事幾乎可說是既唯心而又夢幻。我不願說那是一段架空的情節,我還願意相信人們生命中都擁有一個曉天或者晴恩,又或者我們都當過那個只願享受他人全心的愛卻付出無能的愛莫,我甚至為心有不甘的驕傲的她感覺不捨,都已身在那最後時刻,明明無關愛與不愛,還是不願在情感棋局上棄子:「我不願意讓晴恩知道曉天忘記我了,這是一種恥辱,我不想在晴恩面前認輸,但事實上,在曉天和晴恩之間,我已經不存在。」那是一個意欲證明自己「切實存在」的象徵,透過他人錯認曉天的愛的投向,穩固了愛莫的重量,儘管她如此理解那最初的、「屬於她的」一切皆不再,「失憶」的現實與象徵性,恰恰鋪陳了這故事中為晴恩量身訂作的,也是整本小說中最詩意喟嘆、也最接近夢境的時刻。那也是整本書幾乎唯一以懷柔方式坦白出愛莫(我們)自以為與眾不同、實則害怕就這樣遭記憶(時代/年齡)淹沒的無聲恐懼。而她清楚知道自己別無選擇,對所有人而言,沒有所謂的救贖,也沒有HappyEnding,唯有坦然地(即使一開始是裝出來地)大步向前邁,才有機會一再變換/堅持「自己的」樣子。沒法抵擋命運的嘲弄,至少走也走得看來無畏灑脫。《再放浪一點》原本有個簡潔些、不過確實有點過分話中有話的前書名,我並不確定是作者或是編輯的意思讓《再放浪一點》最末出線,但在讀過原稿幾次之後,我忽然能夠感受到在那些燈紅酒綠卻又相濡以沫的遲暮老派之愛背後,如此看透世情的心有不甘,這讓「再放浪一點」幾個字的積極與活潑完整地妝點了這無名俱樂部的午夜時分。旅行歸來,說故事的人愛莫以自己進行得不甚順利的劇中劇為引,鋪陳了讀者的悲喜情緒也同時暗示了接下來的情節走向。於是我們跟著她們一齊走到了看似荒謬而又縈繞淡淡哀愁的戲劇性轉折點。在看似戛然而止的故事末端,愛莫這樣跟鞏麗蓮說了一句話,大抵總和了這個大齡女子俱樂部的主題:「我覺得梁夢汝會比較希望我們笑,而不是哭。」散場過後,紅絨布幕再次拉開,舞台聚光燈打在主角身上。人生如戲,戲若人生,有時歡天喜地、有時悲傷不能自已。趁燈光還昏暗,女子們便落下那只歪壞的長頸鹿,笑著向未來(過往)跑去。
客服時間:週一 ~ 週五10:00 - 18:00(國定假日除外)
客服電話:02-6633-3529
客服信箱:mf.service@mirrorfiction.com
© 2025 鏡文學 Mirror Fic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鏡文學 App
好故事從這裡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