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輕時創作的《默默》改編成影視劇、出版品《Day Off》(每日青菜 著)售出日本、韓國以及越南外語版權,留守番總編輯黃思蜜也因《Day Off》獲得第十三屆金漫獎漫畫編輯獎,二零二二可以說是黃思蜜的豐收年。
榮獲金漫獎後,黃思蜜在社群中寫道:「小時候想過當漫畫家,沒想到後來當了設計師還開出版社,今天能以漫畫編輯的身分站在金漫獎的舞臺上。」
小說家、設計、一人出版總編到漫畫編輯,黃思蜜的多重身份以及在跨界的亮眼成績,無不讓這世代的眾多的斜槓青年們,好奇這其中的平衡與巧勁。

《默默》 黃思蜜 著
《默默》是他的第一號油畫作品
學畫出身的黃思蜜以素描比喻短篇小說,第一部長篇小說《默默》是他的油畫習作。《默默》描繪完美主義者葉廣,為了爭取父母的認同而投入學生會長選舉。卻被他的對手——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徐啟章——撞見自己愛車被偷的狼狽時刻,兩人在選舉期間,檯面上相互攻防之際,暗生情素。黃思蜜筆下的角色幽默可愛,看似美好的校園日常卻潛伏著霸凌,以及對體制和階級的憤怒。
《默默》的叛逆受到村上龍《69》啟發,黃思蜜轉化學生時期當選班聯會會長後遭受霸凌的經驗,在選舉日隔天,黃思蜜發現抽屜的課本被人寫著不堪入目的字眼,至今不知兇手為誰的他,在《默默》中安排同樣的橋段並讓角色找到幕後黑手。
這圓滿現實中的不如意、轉化現實的手法,也出現在他的短篇小說〈小天使與機器人〉裡,文內人去樓空的一幕來自於他的兒時經驗,現實中與好友失聯的黃思蜜,選擇在虛構中讓兩位角色重逢。黃思蜜也將《滿地都是小星星》裡失志的藝術家江睿陽帶到日本,以江睿陽之名出版旅日隨筆《遊樂園》、舉辦攝影展,還鬧了個大誤會,讓江睿陽這名角色以藝術家之姿登上自由時報。
作者與角色的虛實交織,也反映在《默默》的葉廣與徐啟章上,葉廣下意識討好所有人的性格是黃思蜜圓融的一面,但徐啟章渴望一切毀滅的不甘,則是黃思蜜「中二」的黑歷史。
黃思蜜直言,現在重溫《默默》,就像是凝視著另外一個人一樣。與過往的割裂,也成為黃思蜜日後的課題。
自日本返台後,黃思蜜與幾個好友成立留守番,希望能編輯出日本那樣的具設計感的刊物。幾個夥伴不支薪,不計得失,靠著熱情做出一本本書,這般熱血的工作模式卻因為七年前的一場風波而結束。當時曾有讀者批評,留守番若是關門,都是因為黃思蜜;合作夥伴甚至對黃思蜜說,就算留守番能參加台北國際書展,也不會開心。
就像是重溫《默默》時,已經無法體會葉廣和徐啟章的感情,黃思蜜回憶當時一切,也無法理解自己當時不成熟的應對,現在的他後悔自己若是能早一點認錯,也許當年的夥伴們還能一起工作,一起到台北國際書展。

▲受到村上龍啟發的《默默》。(圖/鏡文學 攝影/鄒保祥)
由租書店的小房間走向國際書展
「我們那個時候的願望其實很小,想將我們的出版品帶到台北國際書展,就覺得BL作品可以跟其他書一起展列。」
黃思蜜回憶,小時候去租書店借BL作品,總是需要進到一間小房間裡,彷彿見不得人似的。就黃思蜜看來,BL就像武俠、推理一樣,只是個類型,在任何地方讀都不丟臉才對。當留守番加入獨立出版聯盟,黃思蜜總算實現年少時期的願望,將BL帶出小房間,與其他類型的出版品一同展示在燈光下。
現在的黃思蜜甚至與旗下的BL出版品一起來到法蘭克福,在黃思蜜眼裡,留守番的蓬勃發展,其實和台灣社會風氣轉變有關。「我們做這件事情只是時間上剛好跟台灣一起成長。我們吸收自由的養分,台灣社會風氣越來越開放,那大家就可以越自由地談論自己想看的東西。」
「一起成長」這一點也對應在BL的「不再夢幻」,黃思蜜分享同志友人們從拒絕BL,認為BL描繪的男男日常太過夢幻,到現在一個個入坑。他認為,這和台灣大環境變化有關,同志們可以想像幸福,十年前那些太過夢幻的Happy End,都不再只出現於小說裡。

▲留守番起家厝。(圖/鏡文學 攝影/鄒保祥)
醜陋大人們(?)的下一步
位於板橋松江街路上的留守番小書店,是「留守番」這個大計畫的子項目:出版有設計感的BL作品、登上國際書展、開書店,黃思蜜一項項完成與夥伴的願望清單,最終走到留守番小書店,抵達當年設下的終點。一路走來不時有朋友勸她,不能靠理想做事,這讓黃思蜜不禁反問:「如果我沒有靠理想做事,那我還能做什麼?」
自大學畢業製作,以自己的裸照為主視覺,對抗先芭比瘦身型的「胖比」包裝盒;旅日時,替筆下的角色江睿揚出書、辦展。黃思蜜靠著理想與衝動,做了不少好玩的事。然而在坐擁資本和經驗後,三十多歲的黃思蜜卻沒有心神再去做「好玩的事」。
黃思蜜以一人出版挑起一切,抗拒將出版事務系統化,是基於保留出版更自由、更接近「人」的特性,好比《一生孤注擲溫柔》這本書,黃思蜜將一本本封面燒穿,透出內頁的文字,以此呼應小說裡的烽火與倖存。若將留守番的出版品一字排開,早年的刊物除了書名外,並沒有文案。黃思蜜說,這是因為在販售現場,編輯自己就是文案,編輯直接與讀者交流,將一本本書交出去。但隨著出版量增加,黃思蜜不只需要盯著成本和銷售數字,也必須將出版變得更「制式」才能量化,這些「妥協」都將當年那些「好玩的事」越推越遠。

▲「我現在就是那樣的大人。」黃思蜜自我調侃。(圖/鏡文學 攝影/鄒保祥)
原先趁著《默默》售出劇集版權,鏡文學曾請黃思蜜改寫《默默》,然而當他試著重寫,才發現自己離那個叛逆的年歲太過遙遠,黃思蜜曾經在《默默》中控訴的大人,竟然已經成了自己。黃思蜜翻開手裡的《默默》,幽幽地讀出當年寫下的句子:「大人如果是這麼醜陋的生物,為什麼要我們漸漸變成那樣?」
「我現在就是那樣的大人。」黃思蜜自我調侃。
在訪問中,黃思蜜時不時把自己是討人厭的甲方掛在嘴上,直呼自己要耗損殆盡。但此刻黃思蜜並沒有休息,他的下一項計畫已經悄悄上線:在留守番新成立的Youtube頻道裡,有著他開店和逛法蘭克福書展的vlog,晃動的手持鏡頭充滿雀躍,畫外時不時會飛出一句「好可愛!」。也許成長便是在冒險和世故間找到平衡,剛好和台灣一同成長的黃思蜜,或許能夠讓留守番的年輕讀者們,對於「長大」有那麼一點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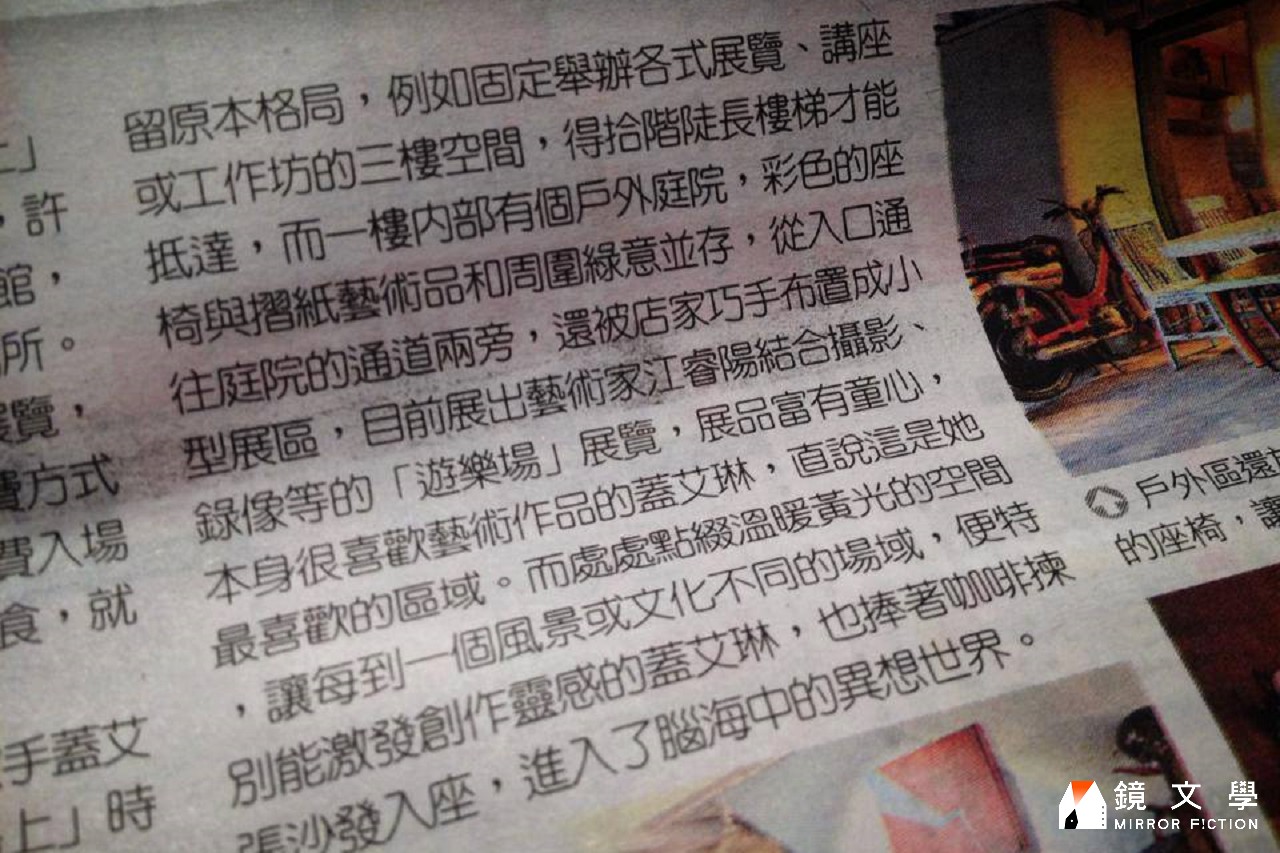
▲意外登上自由時報的「藝術家」江睿陽。(圖/黃思蜜提供)

▲一本本燒灼的手工書,這些都是曾經的「好玩的事」。(圖/黃思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