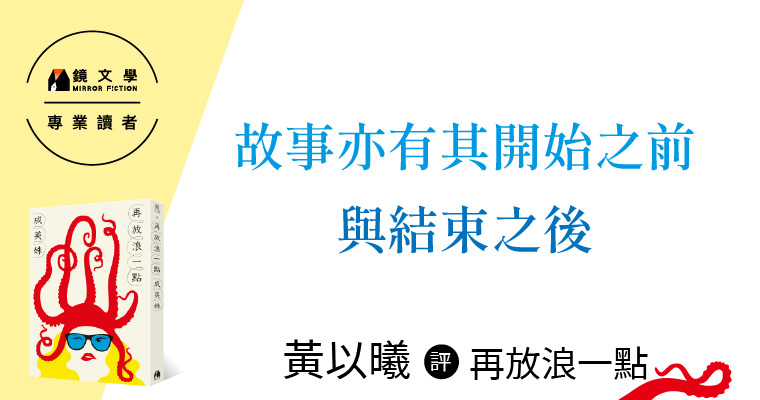
故事亦有其開始之前與結束之後——黃以曦評《再放浪一點》
成英姝的新作《再放浪一點》,是一本關於女人的「我」的小說。但什麼是女人的「我」?當女人說「我」或「自己」,那指的是什麼?得先有自己的房間嗎?是除去性別底蘊、堅守「人」的純粹內涵嗎?在日常、在角色、在關係底,探問「我」,真是可能的嗎?當人們說「多愛自己一點」,那是什麼意思?或者,更令人費解的,「愛自己才能被愛」、「先愛自己才能愛他人」,又是什麼?以及,「永遠要保有自我」,那的需要被保有的是怎樣的東西,且是由誰來保有?《再放浪一點》成英姝 著出版日期:2020/6/12什麼是女人的「我」?在《再放浪一點》,有四個女人,一是書中的「我」,叫愛莫,三十六歲,卡在藝術與商業瓶頸的不得志編劇;一是年輕演員由果,長相和身材俱不盡符合演藝圈標準,發展不順利,但樂天又努力;一是資深也已退役的演員龔麗蓮,念著年輕的風光,找上愛莫為她量身打造劇本,期望再次東山再起;一是跑通告上節目的知名心理學家梁夢汝。愛莫和由果同租一處,龔麗蓮為了劇本也跑來一起住,梁夢汝則是該共居生活中時不時出現的友人。表面上,《再放浪一點》是個非常冷淡的故事。這四個女人在都會浮沈,許多挫折、落寞,有幾乎成為感動的快樂、更多時候則只是日子淡淡到來又離開。四個人生,故事似乎賦予其間的交集與牽動,但到底是錯覺、錯解,因為每處輻臻點,仍由每個人的生命軸線各自定義。換句話說,她們緊密且錯綜地交往相處,但每個生活都是獨立的,甚至透有斷然的氣息。那非關拒絕,非關性格裡的乖僻,而僅僅是,她們都擁有某個絕對性的自我,就算她們自己毫未察覺、也不曾由此去強調。四個人,可以有多少種排列組合,書裡就有多少可供拆解細究的獨立關係,愛莫+由果、愛莫+龔、龔+梁、由果+龔+梁愛莫+由果+龔+梁、……,在並無太多情節起伏轉折底,通過整份疊圖效應,每個人的輪廓漸漸顯明、鮮明,到後來且像是某種執拗,成為了命運般的角色。我們看穿她們每個人是如何來到這一天,而在書頁結束後,又將走向哪裡。她們都是很平凡的人,這裡說的平凡,指那些模板化的表現,即使是抗拒主流、忠於初衷、熱愛或失望於生命,即使是不同於通常女性生命歷程的毫未牽絆於丈夫、小孩、父母,她們仍是我們絕不陌生的樣子:似是而非的人生反省、煞有介事的夢想追尋、關於愛與友誼的入戲唱和……。《再放浪一點》給出一個「自以為可以不世俗,可終究無法不為世俗吞噬」的場景,而在此一時刻,這些女人之於自我審視與評量的誠實,將揭曉,以一般性、共通性處境而言,我們的靈魂在這個世俗裡還可能怎樣窮盡?是否真有任何價值?別的編劇願意遵循商業風向,寫出叫座且也不一定不叫好的作品,愛莫無法是那樣的人;別的女演員忙著醫美瘦身以潛規則搏上位,由果不留後路地深潛入一個配角;別的退役演員默默讓位,讓往事成雲煙,龔麗蓮卻不畏取笑要重新進駐;別的暢銷作家拼代言上通告,梁夢汝卻更浮沈於無止盡內心戲。是的,她們和多數人不同,但真又有那麼特別嗎?而到頭來,假如特立獨行、堅持自我,看起來也沒有更帥、反而錯過更好的待遇,這一切是否徒勞可笑?還是說,正是由這種不值、這種近乎可悲,反過來提示:叛逆是容易的、作自己是容易的,重點不在這裡,而是,反正,面對這樣的世界,人從來就輸無可輸?《再放浪一點》珍貴地勒令關於人生的自主與清明,可以是尋常而當然的選擇,它不為了意識形態的演化或爭奪,亦絕不保證感覺良好,它只是一個應該被直覺地、無條件地納入考量的選項。故事裡,這些女人或有可愛之處,但也跟其之不可愛,不相上下,成為一個「掛念自己是誰」的人,不為了變得可愛,但也非關不可愛。成英姝的作品裡永遠有種頑強的虛無,那不是厭世、不是對(反)價值的捍衛、不是「看透」、亦不是「何必看透」,而是一種對於當下、對於此在的執著。懷抱如此執著,之於流轉的時間與人世,必然脫落。《再放浪一點》亦貫穿著從那樣的由彼個無法成立於任何哪裡的視角,對生命的遙遙凝望。小說中有一部愛莫為龔麗蓮寫的劇本,小說家這樣寫女主角S,「S有一種超乎常人的神經質,以及各種矛盾,她既敏銳又粗率,她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執拗,普通人都知道該遵守的法則毫不在乎。她的問題很多,卻無視於關鍵的答案,她喜歡裝作老於世故,他卻覺得她一派天真。她發現自己在學新的事物,……學著當一個新的人,……她覺得自己就像電影裡的人物。……現在她的生活裡沒有別人,沒人會提醒她過去這一生的線索,她絲毫不想那些。」不意外,但依然驚悚的是,這部戲中戲裡的女主角,或可看為是在將小說中這些女人浮蕩又閃爍的狀態給重新錨定。她們都是S,她們是電影裡的人物,而這是四部分別開來的電影,我們讀到的一個屋簷下貌似女性情誼的種種,終究只是幢幢幻影。那部戲中戲像個玩笑或狂想地毫不合理,又任性或挑釁地關閉。它在小說的中間,某意義而言,《再放浪一點》的都會女性自覺旅程,在終點到來之前,早已公布結局:怎樣戲劇化的人生、潮浪起伏的際遇,都虛假單薄,像個佈景,你配合演了一路,在裡面獲得一些真實,分享一些真實,但你無法在那裡。你是空的。只是,儘管是空的,那些流動的夜晚仍是美的。這份美,是不可能否認的真實,至於那是否讓走一切變得值得,不必是同一回事。女人是雙層的、多層的。如何標記女人的自我?那是統御著增生繁錯的無數自我的更後面、更高的那個「我」。是以,她無法不是透明而淡漠的。《再放浪一點》中的女人,每個都說了很多話,爭相表達辯論著心思,但其實那都不是她們的「我」;真正的她們的「我」,漂蕩在半空,無可無不可地看著自己說話。那每個女人,越是執著深入就越疏離,越是親暱就越冷眼與寂寞。當然,反過來也一樣成立:她們獨自時仍那麼溫暖、充滿關懷,她們和彼此賭氣鬥心機,越是激烈,就有越多「一起孤單」的感激、包容與愛。《再放浪一點》說,人們一生就像在說一個故事,但這故事又包含著無數個小的故事。故事換了方式去看、去說,就成了一個故事,那麼,「故事究竟有沒有它自己?」、「那個它自己又是什麼、在什麼時刻誕生的?」小說家與人物齊聲追索。這或者是個文學的提問,但它亦是個存在的提問。當大故事包含著小故事,並非小故事組合成了大故事,而是,當大故事勾勒邊界和朝向、牽制小故事的生成與擠壓、小故事爭競與求存、而那或者未能改變大故事的類型和格局、卻在裡頭深植了類似情感、價值、幻影與真實的東西。那麼,我們還如何正確「看到」這個故事:「它」是小故事的聚散平衡,還是大故事的始終儼然?《再放浪一點》裡是數個女人的大故事嗎?那些小故事真參與塑形她們各自最後的樣子嗎?而這些女人各自的人生、以及一部部的戲中戲,又在連動地使那一個終極的大故事浮現?而當換置了故事自己的視角,則「我」是變得懸缺而可疑嗎?還是這才是「我」的樣子:清明的距離,卻有肉身無止地牽扯忙碌,由此在不可測的命運彼邊,織就整個對反的模樣,是為「我」?本文作者黃以曦,作家,影評人,著有《離席:為什麼看電影?》《謎樣場景:自我戲劇的迷宮》《尤里西斯的狗》
+ Mor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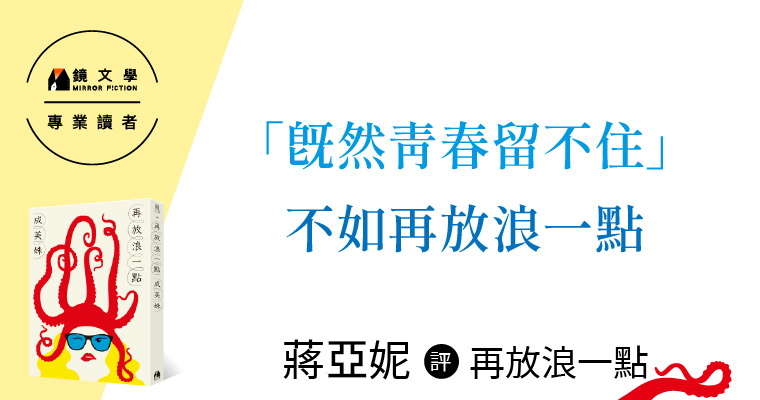
「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再放浪一點——蔣亞妮讀成英姝《再放浪一點》
我很害怕單一化。不管是一件事、一種稱呼、一個版塊或一類性別,比如「女性文學」、「女性作家」與「女性書寫」(替換成同志亦然),但我明白這些存在,依然有其必要性,因為世界確不存在專指男性書寫的「男性文學」,我們只能不斷催熟「其他」、壯大「之外」。《再放浪一點》成英姝 著 出版日期:2020/6/12成英姝的最新長篇《再放浪一點》,距前作《寂光與烈燄》整整四年,男賽車手開出記憶的荒漠,這次的小說主角是三個有欲望、有野心的女性。成英姝只使用了一個進行中的「劇本」,便將三者串連。三十多歲的女編劇高愛莫,一直期待寫出暢銷劇本,卻總是心比手高;五十多歲的過氣豔星鞏麗蓮,將最後翻紅的機會壓在請高愛莫為她打造的劇本上;最後是二十多歲的Z咖女演員林由果,為了演出機會極盡賣傻、賣瘋、賣性感,拋售羞恥。不經意處,有著張艾嘉2004年電影《20.30.40》的女性年齡思考,或許一點1994年王晶電影盛世時期《戀愛的天空》(又作《四個好色的女人》)中的自覺與譏誚,偶爾閃過2013年黃真真執導的《閨蜜》裡,少數精彩大膽的生動對白,疊影混搭。說穿了,《再放浪一點》是講女性的小說,卻不該被單一化為女性小說,這是我深以為戒的閱讀整理。1990年「布克獎」得主,英國作家A.S.拜厄特說過:「如果要做為一個好的女作家,你首先要是一個好的作家,而不是僅僅和女作家在一起,大家只討論女性的事情。」這與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說過的:「在這個世上,我首先得是一個負責任的父親,然後才是一個作家。」放在一起看,相當有趣。事情的優先順序永遠是,先是一個怎樣的人、才是一個怎樣的作家,至於性別,萬萬不需要淪落為少數族群與偏遠地區一般的加分要點。成英姝雖然在《再放浪一點》不斷拿針戳出女性的血點,像是談到年紀時,她寫四十多歲女人的屁股,會從短褲下緣垂出,但穿的卻不是熱褲;可四十多歲也不全然缺點,比如女人拉皮:「都說拉皮就要趁年輕,大概四十多歲最好,拉了能定型,還好看,老了才做,三兩下就崩壞了。」幽默的最高級是開自己玩笑,這點成英姝與她小說中的三個女人都做到了(換成男性處理就容易落得政治不正確)。如果就只停留在此,三個女人一台戲,就算再加上一個暢銷名作家梁夢汝與時尚設計師維若妮卡,五個女人大搞女性主義,唱得也還是過於單調了。還好,成英姝不需要女性加分,她在《男妲》跟《地獄門》等長篇作品裡,已經自證這點。不管是暴力、類型、情色與異色,她都玩過了,所以我們必須看進深處,穿越性別、翻玩意識。大家應該都聽聞過維吉尼亞·吳爾芙那如當代夏娃宣言般的「自己的房間」,女性(尤其寫作者)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房間需能上鎖。不過吳爾芙的原句不只這些,而是:「女性要想寫小說或詩歌,必須有五百鎊年金和一間帶鎖的房間。」散文集《自己的房間》出版於1930年前後的英國,作個簡單計算,那時的500英鎊約等於如今的120萬至150萬新台幣(相近當時英國中產階級以上男性年收入)。吳爾芙與她「500英鎊說」也非憑空發論,剛好是她姑媽留予她的遺產年金。可惜,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民國107至108年平均年收入,當代台灣女性大約落在57萬至60萬間,小說中的三個主角大約也不會超過這個數字。當我們都少有「500英鎊」年收時,就不再寫了嗎?答案很簡單,不管你是男是女、優渥還是落魄,都得要寫。反正生活再慘,小說裡得暫時靠海苔片、泡麵、豆腐撐過生活的女編劇也寬慰自苦地說了:「幾個月接不到工作,明明過著清貧的生活,卻一點也沒瘦,又是一樁宇宙並非邏輯建構的證明。」編劇也好、作家也好、畫家編輯老師都是,拿著筆的一個都逃不了,比起性別,《再放浪一點》的主體,更靠近一群無處可歸、無路可出的現代人。這不禁讓我想到多年前成英姝在「三少四壯集」發表的短文〈我們都太在意永遠〉,她寫喜歡的作家:「托爾金的世界是一個放置在真實的凡俗的平淡無奇的世界中的箱子,兩者平行重疊,當濃霧遮蓋了視線,有時撥開那白色的簾幕,就會置身在托爾金的世界中。有一種電影情節,主角意外或者為了某種目的,來到了另一個時空,大部分的劇情,最後都讓他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這也是我在讀這本小說的感受,當我在小說世界、他者時空,遊歷一場後,卻發現聽到的全是我自己世界的回音與困境。比如,故事的存在可能;比如,美好的總是往日時光。雖然美國小說家勞倫斯·卜洛克聲明:「偽造正是小說的核心與靈魂。」而在一眾台灣小說家中,成英姝很高程度地展演了她虛構(Fiction)的能力,私小說的座位,即使你拿著她生平門票一幕幕尋找,最多也只能看見經過了離解、脫墨、洗滌、漂白而還魂的再生紙,前人的名字與筆跡,你找不到。她是罕有地認真說故事的人,為我們展演她精心設計的一個又一個「靈暈」(aura)。靈暈就像故事的入場卷,你得透過它才能真正進入故事氛圍。她通過小說中編劇角色的困局,狠狠敲擊了當代文學一直討論不休的:該怎麼說故事、還有沒有故事,以及有沒有人還在說故事?於是在小說故事完結前,她忽然花了許多段落定義「故事」:「故事究竟有沒有它自己?那個它自己又是什麼,在什麼時刻誕生的?人的一生說了數不清的故事,這些無窮的故事散亂,充滿矛盾、歧義,它們會被什麼指向一處,變成同一個故事嗎?⋯⋯事實上,每個故事在當下便已完成了,每一個瞬間就涵蓋了過去和未來的可能,在那個點上,它已經是完整的了,有它自己的內在邏輯。」成英姝以故事作答故事存在,故事是有可能的,小說依然在說著不同故事與包裹故事,故事裡又再藏著些許內在自我。小說隨著主線「劇本」的完成,走向結尾,最聰明者顯得蠢笨、最癡傻者卻看得最清,撕逼的人說不定相知相惜,這樣的安排在小說裡並不特別,特別之處是成英姝洞悉世情的口吻,當她寫道別人教訓愛莫的編劇態度時,說的是:「你犯的這個毛病也反映在你的創作態度裡,你鄙視陳腔濫調,你對於無論是別人或者自己曾經說過的話都認為沒有價值重複,但你以為真理有多少?」過去了,才有來處可以回頭,天真過,也才能說世故的語言。我和小說同時驚覺,現在的所有故事,都由「過往」觸發至今,就像五十多歲的昔日豔星高談自己仍有粉紅色乳頭一樣,看似放浪的全是幻夢。每一個小說的角色都困於舊日,尚未發福的身材也好、捧在手心的愛或是充滿可能的未來都結束了,於是小說為他們寫下:「以為永遠記住我們年輕時的樣子,彷彿就能回到過去,但過去就和未來一樣,從不在默默那裡等待。」說的其實是,往日時光,早已遠去。「回不去」的不只叫半生緣,方文山為南拳媽媽寫的歌裡,那年Lara也唱著:「到不了的都叫做遠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鄉。」小說中的每個人,似乎也都無家鄉、無歸途。既然無家無鄉(也沒有吳爾芙說的百萬年金)、既然青春終究留不住(也活不成李宗盛一樣的成功大叔),成英姝告訴我們,不如再放浪一點,反正,沒有從前了。
+ Mor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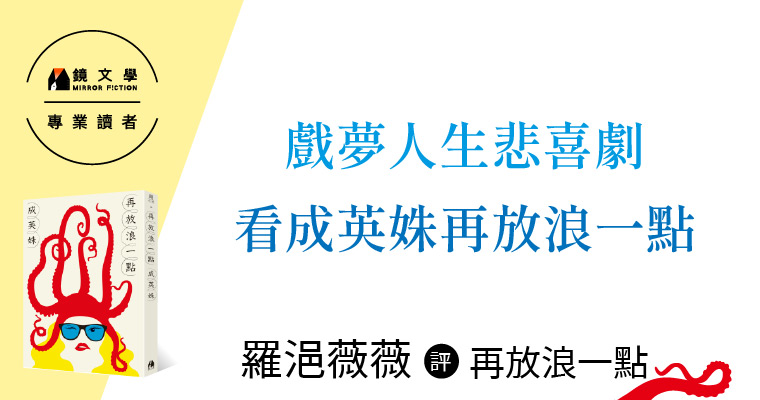
戲夢人生悲喜劇——羅浥薇薇看成英姝《再放浪一點》
我有一群不三不四的朋友,在臉書上開了個名為「D級俱樂部」的私人群組,裡頭有大學教授、家庭主婦、烘豆師、海外遊子、動畫師、無業遊民、藝術家等等共計十一人。這是個第一時間很難令人理解的神秘組合,但裡頭或積極或潛水、身懷各自武功門派的成員,加上版面裡每日的插科打諢與世界奇聞轉帖,讓這俱樂部從一開始的無心插柳到而今的藤漫成牆,人人皆從自甘低級的嘲諷底下尋出最小眾的樂子,並深深相信彼此必定能理解其中暗語。《再放浪一點》成英姝 著出版日期:2020/6/12看了《再放浪一點》,我一直在想自己的D級俱樂部,認真思索著此類秘密結社之必要。說秘密,其實這並非一開始便得說出口的要件(畢竟說得出口的就不叫做秘密了),而是一種氣味,加上(聽起來無比老套的)緣分。於是我們得到了愛莫、梁夢汝、鞏麗蓮、由果,四個陰錯陽差、既排拒又親暱的角色,成英姝描摹人物,尤其女性,真是一絕,相較起她眼底各形各色環肥燕瘦的都會女子,所有的男性都成了配角。她擅於運用活靈活現的人物及情節帶動故事的節奏感,那些對話尤其簡練精彩,你完全可以想像它被改編成舞台劇:「我小時候好嚮往院子有游泳池的房子,我心想,得多有錢的人家才擁有游泳池啊?」由果說。「人總是會嚮往沒有用的東西,要游泳池到運動中心就好了,買月票才1500,不限次數。你知道養一個游泳池要花多少錢?還沒有跑車實際。」鞏麗蓮說。「你都到公立運動中心游泳?」我問。「當然不!我是女明星,給人認出來怎麼是好?」鞏麗蓮說。「她都去那種養生游泳池,有三溫暖和草藥浴的,草藥池裡頭還放薑,老人都去那兒。」梁夢汝說。由果的天真爛漫、愛莫的追問者性格、鞏麗蓮與梁夢汝的看來互相吐槽實則交心至深,四個人從面部表情到人生觀,在這個場景輕描淡寫的幾句話之中便生動描摹出來。成英姝筆下的都會女性,所需面對最波濤洶湧的,已並非社會架構底下的客觀性別困境,更多是直面規範之後自我與他者的對話,而這個「自我」與「他者」在《再放浪一點》裡,實為一體兩面、無法分割。愛莫在看待與書寫身邊各色女子的同時,看似客觀辛辣自有想法,但深究之後我們會發覺,所有的想法之中都包含著她對自身、人際、乃至於整個社會的的主觀想像。作為一個說故事的人,如同《傷心咖啡店之歌》裡頭的馬蒂,成英姝在故事裡藉主角的囈語,像在鏡子屋那樣撫著鏡中的自己,一面自問自答、苦於毫無出路,一面仍捨棄不了內心深處對於(儘管可能永遠走不到的)洞穴盡頭那絲光亮的一抹想像:「人的一生說了數不清的故事,這些無窮的故事散亂,充滿矛盾、歧義,它們會被什麼指向一處,變成同一個故事呢?」「……,但事實上,每個故事在當下便已完成了,每一個瞬間就涵蓋了過去和未來的可能,在那個點上,它已經是完整的了,有它自己的內在邏輯。人或可以眷戀、頻頻回首、躊躇未知,但活著這件事只發生、結束在當下片刻,不仰賴倒帶或者不確定的未來,因為它自己就是過去與未來。」四個個性迥異的女人們在鋪陳了大半篇章後,終於拋開俗世種種、真正地乘著噴射機離去,在旖旎南國共處一室。你若曾經計劃這樣的旅行過,便能理解最理想的旅伴不是愛人,也不好是與你太過相似的人,這有點難解釋,大致就像小說裡四位女主角那樣,可以瘋癲可以拌嘴可以完全接住你,但絕不輕易把「包容」說出口。在異鄉的放大鏡之下,你會發現自己的開放性與想像力都水漲船高,角色性格與故事走向至此漸漸收攏而愈見清晰,那就算快被現實磨損殆盡也難全然捨棄的溫柔慈悲由此淡淡浮現。我是從曉天與晴恩的支線看見那溫柔的。相較起小說中其他人物之間的關係與對話,這段故事幾乎可說是既唯心而又夢幻。我不願說那是一段架空的情節,我還願意相信人們生命中都擁有一個曉天或者晴恩,又或者我們都當過那個只願享受他人全心的愛卻付出無能的愛莫,我甚至為心有不甘的驕傲的她感覺不捨,都已身在那最後時刻,明明無關愛與不愛,還是不願在情感棋局上棄子:「我不願意讓晴恩知道曉天忘記我了,這是一種恥辱,我不想在晴恩面前認輸,但事實上,在曉天和晴恩之間,我已經不存在。」那是一個意欲證明自己「切實存在」的象徵,透過他人錯認曉天的愛的投向,穩固了愛莫的重量,儘管她如此理解那最初的、「屬於她的」一切皆不再,「失憶」的現實與象徵性,恰恰鋪陳了這故事中為晴恩量身訂作的,也是整本小說中最詩意喟嘆、也最接近夢境的時刻。那也是整本書幾乎唯一以懷柔方式坦白出愛莫(我們)自以為與眾不同、實則害怕就這樣遭記憶(時代/年齡)淹沒的無聲恐懼。而她清楚知道自己別無選擇,對所有人而言,沒有所謂的救贖,也沒有Happy Ending,唯有坦然地(即使一開始是裝出來地)大步向前邁,才有機會一再變換/堅持「自己的」樣子。沒法抵擋命運的嘲弄,至少走也走得看來無畏灑脫。《再放浪一點》原本有個簡潔些、不過確實有點過分話中有話的前書名,我並不確定是作者或是編輯的意思讓《再放浪一點》最末出線,但在讀過原稿幾次之後,我忽然能夠感受到在那些燈紅酒綠卻又相濡以沫的遲暮老派之愛背後,如此看透世情的心有不甘,這讓「再放浪一點」幾個字的積極與活潑完整地妝點了這無名俱樂部的午夜時分。旅行歸來,說故事的人愛莫以自己進行得不甚順利的劇中劇為引,鋪陳了讀者的悲喜情緒也同時暗示了接下來的情節走向。於是我們跟著她們一齊走到了看似荒謬而又縈繞淡淡哀愁的戲劇性轉折點。在看似戛然而止的故事末端,愛莫這樣跟鞏麗蓮說了一句話,大抵總和了這個大齡女子俱樂部的主題:「我覺得梁夢汝會比較希望我們笑,而不是哭。」散場過後,紅絨布幕再次拉開,舞台聚光燈打在主角身上。人生如戲,戲若人生,有時歡天喜地、有時悲傷不能自已。趁燈光還昏暗,女子們便落下那只歪壞的長頸鹿,笑著向未來(過往)跑去。
+ Mor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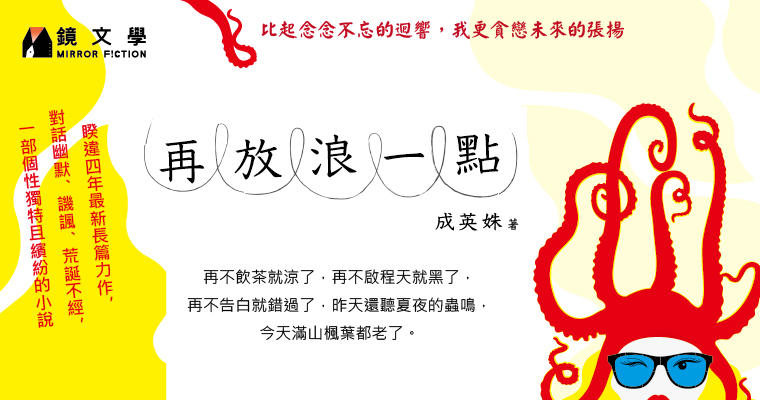
【鏡文學出版】再放浪一點
《再放浪一點》成英姝 著出版日期:2020/6/12★睽違四年最新長篇力作,對話幽默、譏諷、荒誕不經,一部個性獨特且繽紛的小說。──人生演到這,明明覺得自己是明星體質卻老是在跑龍套?──如果你因為《公主徹夜未眠》知道成英姝,你會因為這一本更貼近她,以及你自己。中年之後,成英姝以幽默直視人生的荒誕與缺口,筆鋒再次綻放,將我們的人生寫成一場喜劇。---------過氣女星鞏麗蓮,找上了自認懷才不遇的編劇高愛莫,拉著行李闖進愛莫與室友C咖演員林由果的生活,要愛莫為她量身打造劇本,從此個性南轅北轍的三人共居一室──接下工作的愛莫,劇本總被說只有自己看得懂,卻抱怨起鞏麗蓮的過往無趣,而鞏麗蓮在意的卻只有床戲跟吻戲;林由果則用盡心思搏上位,希望能爭取在大導演的片中擔任配角。就在林由果電影殺青之後,鞏麗蓮提議三人共遊泰國,愛莫認定鞏麗蓮將不久於世,才急著留下代表作,而林由果仍然玩世瘋狂,卻不知即將迎接人生最戲劇性的轉變……隨著越趨瘋狂的旅程,愛莫為鞏麗蓮撰寫的劇本也隨之越來越清晰。三人的人生劇本,最終走到轉折點──可能將她們往人生高處推去,或是往人生谷底推落……再不飲茶就涼了,再不啟程天就黑了,再不告白就錯過了,昨天還聽夏夜的蟲鳴,今天滿山楓葉都老了。作者簡介成英姝一轉眼寫了二十幾年的小說,世界是莫比斯環,一路直直走,正面都成了反面,黑成了白,左成了右,看著煙火燦爛,看著煙火熄滅,聽筵席的喧囂,送離人散去,沒有迴響的念念不忘,無人站在燈火闌珊,生命是陰差陽錯,北極最後一塊冰層破了,科學家預測再五十年人類走向滅亡,人生在世只有當下是真。今年的願望吹牛不打草稿,微老不尊,立地成魔。著有《公主徹夜未眠》、《寂光與烈焰》等。購書連結博客來誠品金石堂讀冊
+ More
成英姝談新小說—因為死亡很近,所以要《再放浪一點》
如果寫作是作者用筆努力抓住世界,生命的吉光片羽——童年嘗過的瑪德蓮,女人在檯燈下如米色蛾翅的睫毛,那場落在全都柏林與死者身上的雪。成英姝寫《再放浪一點》,卻開始「放掉」了。「以前寫作於我是那裡有好美的極光,我也想讓你瞧瞧,現在我會想你沒看見,關我什麼事?」一身長版寬T恤,紮起黃褐色頭髮的成英姝說。我想寫活得理直氣壯的女性是退化嗎?毋寧是更自在的境界。只是這自在求不得,而是哀樂中年後的自救之道。成英姝1994年出版《公主徹夜未眠》,在荒謬見人生的悲哀真章,1998年《好女孩不做》寫乖順背後的冷酷異境,2000年寫推理小說《無伴奏安魂曲》卻也反推理,殺戮變得虛無,寂寞才是釀罪。凡此種種與以降之作,都帶有手術刀般的銳利直取。這一回她寫《再放浪一點》,三個不同年紀身處娛樂圈的女性故事,有編劇、新興演員、過氣演員,都在娛樂圈外圍,努力靠近核心。有人成功了,有人放手,有人死了。聽起來一點都不逐夢勵志,成英姝說,「為何人們都想變得越多人知道越好,覺得這就是成功?我只是想寫有生命力的女人,她們活著,且活得理直氣壯。」所以失敗不是失敗,是你活過的未境之路。好女孩不做也沒關係,風風火火一回就夠。這也是成英姝的人生哲學,「現在寫東西我自問:『我想證明什麼?』或許是寫的片刻我有沒有努力做到活著的感覺,角色活著我就活著。所以寫小說我注重暢快感,甚至不覺得小說是虛構的。」我們習慣看到青春正盛的男女主角在三幕劇結構中受挫、成長,但《再放浪一點》反過來聚焦若有所失的中年後女性——「現在」好像沒有不好,然而再往前, 會觸底還是昇華?人生最難,便是難在不知該向前還是原地解散。沒有一番成就,沒有婚姻倚靠,女性該何去何從?成英姝敏銳捕捉這些感覺人生有點不對勁的女性,浮沉在自我與外物之間的險象。▲成英姝很早便因小說《公主徹夜未眠》聞名,被冠以天才作家、黑色幽默女王等名號。寫作多年,她說寫小說的過程就像在小說裡活一遭,上一本《寂光與烈焰》寫了五年,「簡直像在裡面住了一輩子。」《再放浪一點》雖僅花半年寫完,但背後是她近年對人生的想法轉折。(圖/鏡文學)不證明你自己,你就不存在《再放浪一點》三位主角中,「愛莫」是編劇,創造角色;她的室友「由果」是小演員,詮釋角色;愛莫的雇主——過氣女明星「鞏麗蓮」——則希望重新獲得角色。換上面具,扮演「角色」在小說裡變成一種渴望,驅使她們向前。成英姝說,「如果你不證明自己的存在,你就不存在。所以我的角色都是很自我中心的人。」除了自我中心,她筆下角色也幾乎是不傳統的女性,公主可以徹夜未眠,女流之輩似魔術也像奇花,「有時我也覺得奇怪,為何我筆下人物都無法好好談戀愛,結婚生子,當一個合格的妻子或母親,總是對抗傳統價值觀。但我不是故意的,因為我就是沒有這樣的經驗,也無法想像跟別人建立家庭。」成英姝善寫兼具刁鑽與美的女人,所以《再放浪一點》同樣有不甘平淡的女性,「我沒有刻意展現某種價值觀,對我來說那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就是寫不出別種樣子。」沒有別種樣子,就是成英姝。她說,「作家找尋自己的語言,是為了什麼?為了美學?不是,是找出你自己的角度。找出原來這就是『我』。你怎麼寫就是你怎麼活。」採訪到一半,成英姝點的拿鐵來了,便說好漂亮要拍張照。於是她開始選角度,擺姿勢,談攝影。「拍東西也讓我感到視角的重要,每個人看事物都是跟別人完全不同的角度。所以攝影對我來說就是展現『我怎麼看』。拍食物很尋常,可是一桌的人每個人都拍得不一樣。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每個時刻你用自己的視角看每個東西,串連起來,就這樣過了一生。」小說寫二十、三十、五十的女性,有的敢衝敢撞,有的裹足不前,還有鉛華洗盡,卻重新照見自我的,都是成英姝怎麼活的證明,「常有人問我某角色是不是我的寫照,其實整本書都是我,都是我站在她們的視角想出的,都是我的一部分。」因此,《再放浪一點》帶著成英姝專屬的灑脫。縱使寫娛樂圈,《再放浪一點》不紙醉金迷,而是透過女性在這由男性凝視建構的場域襯托其虛偽。小說幾位女主角最放飛自我的時刻,則讓人想起珍・芳達演的《同妻俱樂部》,笑鬧間,人生熙熙攘攘、兵馬倥傯都可以是姐妹的下午茶時光。▲拿鐵上桌,成英姝喬角度拍照。她興趣廣泛,從攝影到靈修甚至賽車,自言一直以來都對次文化潮流很有興趣,「因為次文化潮流是生命力的展現,有最多最新鮮的熱情。」(圖/鏡文學)死亡在前,你要留下什麼?《再放浪一點》其中一條主線是鞏麗蓮請愛莫為她量身打造劇本,因為可能命不久矣。生命花火最終,誰都想再亮一回。因此,小說無可免的觸碰死亡議題,但讀者可能會跟著笑。現實中,成英姝接連遭遇親友過世,一開始是養了多年的狗,隔一個月後她父親過世,兩年後她妹妹在她出國時動手術,兩個星期後也走了。最近她又送走交往二十年的男友。疫情期間,時不時傳來她對岸朋友突如其來失去身邊親人,「生命竟就是如此輕易無聲無息灰飛煙滅。」「現在我已經做好準備隨時會走。時時刻刻我都在想,人生說走就走,我留下了什麼?每天都在找答案,但找不到。」死亡已被預知,成英姝說那就活在當下吧,「但我發現活在當下不是把握什麼,而是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這些都不想。我的過去與現在無關,而我的當下也不影響我的未來,因為我連明天有沒有都不知道。」話雖如此,成英姝說死前還是有一定要做的事:刪掉電腦裡的草稿跟未完成作品。作品不重要了嗎?成英姝說,「沒了就沒了吧。」好像中年以後人生就是不斷的救死扶傷,直到自己成為最後一個。聽起來中年後就是一路下坡,但成英姝用喜劇面向死亡,她說寫《再放浪一點》寫到她自己都會笑。▲她第一個刺青是十年前刺的。本來不知道刺啥,但有一天想開,就果斷去刺了。會不會後悔刺青圖案?成英姝說,「會啊,人生就是一定會後悔,但誰在乎呢?人生不就這樣嗎?想法一定會改變。人生如果沒有改變,多可怕?」(圖/鏡文學)努力在現世與虛擬獲得補償《再放浪一點》最浪最好笑的是女人間的脣槍舌戰。成英姝愛寫對話,尤其是麻利的對話,「我喜歡表達人,要強調一個人的個性,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她的語言。」同時她愛講話,國小沒什麼朋友,上課卻總是跟坐旁邊的同學發表自己的見地,「那人甚至不是我朋友,我只是想說話。」以前跟作家友人動輒在咖啡館聊七八個小時也不會累。聽起來成英姝很需要熱鬧,可是她又享受絕對的自由與孤獨,想到再談戀愛,心中會牽絆他人,就讓她打退堂鼓,「所以一個人過活就好。」看似瀟灑,連作品都不在乎,但成英姝還是有生活之必須——寶可夢。難道不寫作時都在抓寶嗎?成英姝說,「寫作和抓寶並不衝突。事實上,遊戲跟人生一樣是虛擬的,虛擬的程度沒有不同。」然而,成英姝其實有段時間沒玩,重新迷上寶可夢是在她男友喪禮上,遇見二十多年來幾乎沒聯絡的男友姐姐。等火化時,成英姝發現他姐姐在抓寶,於是也跟著抓。對方還教她新出的團體戰要怎麼打。聽起來像卡繆《異鄉人》裡的情節,只是沒有人被抓去審判。女主角愛莫在裡頭說:「我認為戲劇的誕生,來自一種補償作用,對現實、真實生活的補償。」成英姝說寫小說也是這樣,「我覺得這是我可以一直寫下去的原因。」所以現世裡有很多遺恨嗎?要用小說給自己一個交代。就像她手臂上的刺青,也是給自己的交代——當初是為了證明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我有你沒有才刺的,「現在我發現其實我跟別人本來就不一樣啊。」「不過至少死在哪裡時,別人馬上就知道是我的屍體。」成英姝摸著手腕上象徵靈性的蛇圖騰說。也似撫起發癢的傷口。《再放浪一點》新書上市博客來:https://reurl.cc/MvLbXp誠品:https://reurl.cc/ZOqrXW金石堂:https://reurl.cc/4Rv4QD讀冊:https://reurl.cc/NjLpqk
+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