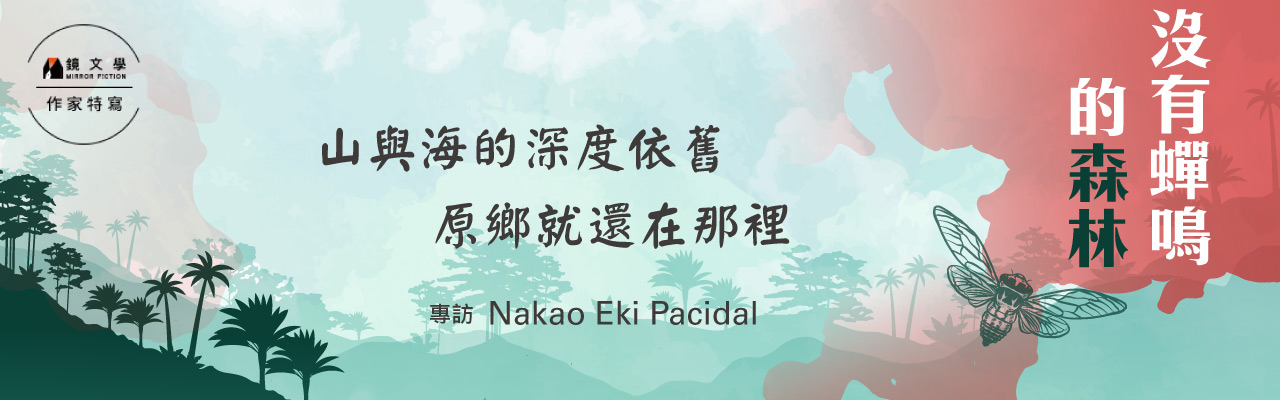山与海的深度依旧,原乡就还在那里——专访Nakao Eki Pacidal
文|翟翱
2020-06-08
Nakao Eki Pacidal 人在荷兰。疫情当前,人间艰巨,我们透过Telegram联系,Nakao谈创作,像遥远的召唤,召唤她笔下的山风海雨,以及这座岛屿的另一种可能性。
原住民身分曾让她自我怀疑
Nakao是花莲太巴塱部落阿美族人,现年四十五岁。虽然她的小说常以部落为场景,然而在台北出生后,除了在花莲念小学外,直到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前都在台北。在都市成长,会不会感到格格不入?她说投票时最有感,因为原住民要投山地或平地原住民立委,而投票箱前往往只有她一人。
这话谈得轻松,成长过程中还是不免被异样看待,「我小学经常被同学笑,有次哭回家,爸妈说不要理他们就好,两三次后也就习惯了。第一次真正感受自己跟别人不同,是高三考大学时以原住民身分加分。后来回想,当时(1992年)考大学压力之大,难免有同学对此感到『不舒服』。」
原住民考试加分听起来像身分带来的红利,然而Nakao说所有曾动用这加分权益的原住民心里都有阴影,会怀疑是不是没有加分自己就没资格上大学。「因为国家没有给我们及非原住民正确认知这权益是从哪里来的,以及这不是为了个人,而是整个群体。即使我在大学、职场都受肯定,可是直到我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才觉得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尽管从来没有人质疑我。」
「无可避免,我们在看别人时总是去脉络。」或许这正是她台大法律系毕业后,横跨不同领域,从科学史到欧洲史、史学方法的原因。同时,她自言对纯知识非常有兴趣,创作也不限于原住民元素,奇幻穿越、历史宫廷,甚至BL,都在她点化之下成为小说长河的金沙。

▲2014年,Nakao Eki Pacidal 参与原运,在路边进行阿美族语教学。摄影/Savungaz Valincinan
藉小说展示不同的文化框架
2009年,Nakao赴荷兰念历史博士,2017年定居当地。2014年,她出版「台湾原住民族当代传说第一部曲」《绝岛之咒》,藉一桩原住民研究生离奇死亡,带出赛夏族矮人诅咒之谜,以及环绕这座岛屿,如月牵引潮汐,影响主角的各式咒念。最终,主角们合力投身创作,想透过文字解除宿命般的咒力。
一如夏宇的诗,「只有咒语可以解除咒语/只有秘密可以交换秘密/只有谜可以到达另一个谜」。图腾与禁忌,在Nakao笔下不是迷信,而是观看世界的不同框架。《绝岛之咒》有十万多字,Nakao却在一个月内写完。她说当时内心浮现不得不写的念头,「《绝岛之咒》其实是我博士论文的小说版,谈传统流失后,文化怎样延续?文化如果是理解自己和他者的钥匙,钥匙不见了,我们要怎么打开锁?」
「这其实关乎你怎样认知世界。在现今科学体系下,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其上没有神灵或信仰,当人类觉得万物都可以掌控,就会无限扩大,沦为贪婪。所以科学也是一种迷信,仅是理解世界的框架之一,不是绝对。」
《绝岛之咒》表面上讲咒力,其实呈现了文化渗入肌理,牵引主角命运,「这样透过小说传达世界观,也符合原住民的史观。原住民不会讲大道理,只会坐下来跟你说故事,让你自己摸索。因为道理过了两三代就会被遗忘,可是故事可以一代代口传下去。」
Nakao说演讲时若谈到祭典、禁忌等内容,开始前往往要酌酒点烟「告知一下」祖先。有几次忘记她「祭祖」,结果讲到一半不是屏幕黑掉,就是麦克风没声音。在外人看来或许是迷信,但一如她对科学的说法——世界是复数的,存有很多观看的方式。有时,我们只需静静领受。
小说来自博论,Nakao坦言《绝岛之咒》是累积十多年思考而成,写完后一度以为自己要再等十年才能写出下一本。岂料之后她笔力雄健,陆续写了好几部长篇:《一个没听说过的燕云旧梦》以今昔对比,谈相声没落;《巡台御史六十七与来自远方的科学家》借穿越形式解答历史谜团;《天为谁春》在虚实之间写纳兰性德生于权贵却长于词人的哀乐;《掌上珊瑚》以怀抱演艺圈梦想男子遇上满族少女为主轴,谈文化认同与被入侵;《维也纳之春》则是原住民追寻自我,远赴欧洲成为音乐家,摆荡在不同文化之间。
对此,她说这跟2017年开始与镜文学合作有关。「以前我是冲动型的人,做一件事要全部投入,结果就是整个人挂掉。写《绝岛之咒》时,白天写博论,晚上写小说,写完好几天下不了床。2017年我开始培养规律,写作如果没办法写满字数,那就写满时数。也因为以前不规律,现在遵循规律,对我来说反而很有趣。」

新小说思辨正义的彷徨时刻
新作《没有蝉鸣的森林》以一场利落的暗杀起头,结合政治议题与成长故事,是原住民版的恋爱加革命叙事;叙述原运团体因土地议题组织恐怖攻击,岛上政客成为目标,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主角泰雅族人「徘徊」是小报记者,被指派追查两名亲中商业大亨及政界人物谋杀案,正当舆论将矛头指向独派人士之际,却在凶案现场发现以阿美族语写的密码,同时他过往心仪同学「歌乐」出车祸。徘徊开始怀疑,岛上无声的杀戮与他大学时期的原住民同学有关。本该歌颂的青春,在死亡的阴影下成为遥远的余音,革命也终归幻灭。《没有蝉鸣的森林》探问何者才是正义?追求正义而行不义之事,又该如何自处?
Nakao说,这类基进声音确实存在原运里,尤其是涉及土地正义或祭典时,「因为祭典是最不能妥协的东西,土地则是失去后就拿不回来了。」1997年大学毕业后她担任国会助理,在前辈提携下踏入原运,到今天已超过二十年,坦言「很多内伤」,「主流外界给我们压力,部落对我们则有期待。一旦离开部落再回来,部落人们看你的眼光就会不同。问题是,你不是每次都能符合他们的期待。在外你要冲撞,在内又要『学习』、『受教』,很消耗。」
创作原住民文学,可以响应他们的期待吗?「我只能实践,不能掌握结果。现在我理解如果要投身运动,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别人的反应可能不如你期望,所以最好不要抱期待。同时学会把时间拉长来看,对自己好过一点。」
因此,她现在看待小说「有作者的思想,可以提供另一个理解世界的框架,当然最好。不过我更多作品出现原住民时,往往是小小的配角。我想让原住民变成很寻常的背景,因为现实中你遇到的原住民就是一般路人,是很自自然然的,就像同性恋也是。唯有被歧视过的人,才会珍视自自然然这件事。让焦点下的角色身分复归平淡,成为读者的日常,是我身为创作者可以做到的小小的事。」现在她写小说如做运动,「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做小小的贡献,累积二十年就会很可观。」
若说《绝岛之咒》是试图用不同的文化框架展示台湾,《没有蝉鸣的森林》则是原汉两个不同文化框架的正面冲突。蔡政府上台时,小英曾以总统身分为百年来原住民受汉人歧视压迫道歉,然而传统领域问题仍未解。政府推动转型正义,却不包括原住民,也让Nakao错愕,「更令我惊讶的是,我身边很多汉人朋友在政界跟社运界,却没有发声,连表示遗憾都没有。那时我意识到,或许总有一天,我跟汉人朋友会站在对立面。」

▲Nakao Eki Pacidal 摄于欧洲友人家。
身处欧洲助她思考原汉关系
此外,身在欧洲也让Nakao思考文化冲突,对位原汉关系。「欧洲最大问题是恐怖主义,我跟欧洲人聊天说,当有别于欧洲文化的东西跑到你们眼前,你们就觉得『无法理解』,归咎于文化冲突。然而明明是可以理解的,否则我们如何理解西方。所以重点其实是『单向性』,归根究底便是懒得理解他者。就像原住民哪个不是在汉人主流社会长大,一生都在努力贴近主流,汉人却无法反过来理解原住民。」
因此,当森林没有了蝉鸣,「暴力,是最后也最大声的语言。」尽管如此,小说最后,Nakao仍以极温柔的语言接住了里头人物的殒落:
「重峦迭嶂的雪山山脉就像呼应大洋一般,也有一半隐身在浅蓝灰色厚重的云里。又是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春日午后,但这岛屿的不论山巅海滨还是城市里,都有人为岛屿的无知无言付出了能够付出的最大代价。」
在所有物是人非里,唯有山与海依旧,以同样的心。访问里,Nakao常说自己老了,心态变了。现在她放弃完美主义,「以前从事原运会受伤,就是因为原运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政治运动要折冲衡量,正义却是无法妥协的。」或许,《没有蝉鸣的森林》她最后想接住的,也包括曾经的自己。
后记:名字,还有过去可言吗?
《绝岛之咒》曾提到:「名字,还有过去可言吗?」小说里,名字也是咒的一部分。她的名字也有段来历,她2007年登记族名和族别,然而现行法律不允许使用没有汉字的名字,所以她不愿用汉字写族名,因此并没有改掉汉名,而尽量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族名。不过因为她多数时间在国外,且护照上使用的是族名,所以形成很诡异的情况——她在台湾以外的所有地方都可以不用汉字来写族名。
我问她这名字有何涵义(其实我很怕这问题给她一种「汉人设想原住民名总带有草木鸟兽意义」的猎奇感)?Nakao为我解答,「这名字本身倒没有意思,就只是名字。Nakaw是阿美族常见的名字,在很多老部落都有Nakaw作为母亲(祖先)的传说,在太巴塱也是。歌谣里也有提到Nakaw是太巴塱的三个母亲之一,奇美部落也有类似的祖源歌谣,不过,Nakaw是标准的阿美语写法,我的名字写成Nakao,是因为家里比较日化,采用日语拼法。」
所以,名字真的有过去,也需要争取,才能真正属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