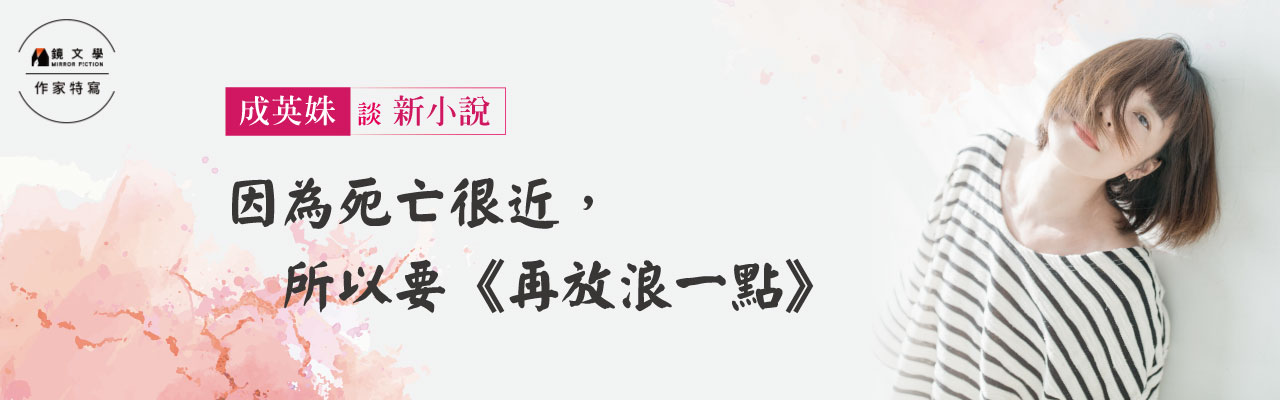成英姝谈新小说—因为死亡很近,所以要《再放浪一点》
文|翟翱 摄影|林炜凯
2020-06-05
如果写作是作者用笔努力抓住世界,生命的吉光片羽——童年尝过的玛德莲,女人在台灯下如米色蛾翅的睫毛,那场落在全都柏林与死者身上的雪。成英姝写《再放浪一点》,却开始「放掉」了。
「以前写作于我是那里有好美的极光,我也想让你瞧瞧,现在我会想你没看见,关我什么事?」一身长版宽T恤,扎起黄褐色头发的成英姝说。
我想写活得理直气壮的女性
是退化吗?毋宁是更自在的境界。只是这自在求不得,而是哀乐中年后的自救之道。成英姝1994年出版《公主彻夜未眠》,在荒谬见人生的悲哀真章,1998年《好女孩不做》写乖顺背后的冷酷异境,2000年写推理小说《无伴奏安魂曲》却也反推理,杀戮变得虚无,寂寞才是酿罪。凡此种种与以降之作,都带有手术刀般的锐利直取。
这一回她写《再放浪一点》,三个不同年纪身处娱乐圈的女性故事,有编剧、新兴演员、过气演员,都在娱乐圈外围,努力靠近核心。有人成功了,有人放手,有人死了。听起来一点都不逐梦励志,成英姝说,「为何人们都想变得越多人知道越好,觉得这就是成功?我只是想写有生命力的女人,她们活着,且活得理直气壮。」
所以失败不是失败,是你活过的未境之路。好女孩不做也没关系,风风火火一回就够。这也是成英姝的人生哲学,「现在写东西我自问:『我想证明什么?』或许是写的片刻我有没有努力做到活着的感觉,角色活着我就活着。所以写小说我注重畅快感,甚至不觉得小说是虚构的。」
我们习惯看到青春正盛的男女主角在三幕剧结构中受挫、成长,但《再放浪一点》反过来聚焦若有所失的中年后女性——「现在」好像没有不好,然而再往前, 会触底还是升华?人生最难,便是难在不知该向前还是原地解散。
没有一番成就,没有婚姻倚靠,女性该何去何从?成英姝敏锐捕捉这些感觉人生有点不对劲的女性,浮沉在自我与外物之间的险象。

▲成英姝很早便因小说《公主彻夜未眠》闻名,被冠以天才作家、黑色幽默女王等名号。写作多年,她说写小说的过程就像在小说里活一遭,上一本《寂光与烈焰》写了五年,「简直像在里面住了一辈子。」《再放浪一点》虽仅花半年写完,但背后是她近年对人生的想法转折。(图/镜文学)
不证明你自己,你就不存在
《再放浪一点》三位主角中,「爱莫」是编剧,创造角色;她的室友「由果」是小演员,诠释角色;爱莫的雇主——过气女明星「巩丽莲」——则希望重新获得角色。换上面具,扮演「角色」在小说里变成一种渴望,驱使她们向前。成英姝说,「如果你不证明自己的存在,你就不存在。所以我的角色都是很自我中心的人。」
除了自我中心,她笔下角色也几乎是不传统的女性,公主可以彻夜未眠,女流之辈似魔术也像奇花,「有时我也觉得奇怪,为何我笔下人物都无法好好谈恋爱,结婚生子,当一个合格的妻子或母亲,总是对抗传统价值观。但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无法想象跟别人建立家庭。」
成英姝善写兼具刁钻与美的女人,所以《再放浪一点》同样有不甘平淡的女性,「我没有刻意展现某种价值观,对我来说那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就是写不出别种样子。」
没有别种样子,就是成英姝。她说,「作家找寻自己的语言,是为了什么?为了美学?不是,是找出你自己的角度。找出原来这就是『我』。你怎么写就是你怎么活。」
采访到一半,成英姝点的拿铁来了,便说好漂亮要拍张照。于是她开始选角度,摆姿势,谈摄影。「拍东西也让我感到视角的重要,每个人看事物都是跟别人完全不同的角度。所以摄影对我来说就是展现『我怎么看』。拍食物很寻常,可是一桌的人每个人都拍得不一样。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每个时刻你用自己的视角看每个东西,串连起来,就这样过了一生。」
小说写二十、三十、五十的女性,有的敢冲敢撞,有的裹足不前,还有铅华洗尽,却重新照见自我的,都是成英姝怎么活的证明,「常有人问我某角色是不是我的写照,其实整本书都是我,都是我站在她们的视角想出的,都是我的一部分。」
因此,《再放浪一点》带着成英姝专属的洒脱。纵使写娱乐圈,《再放浪一点》不纸醉金迷,而是透过女性在这由男性凝视建构的场域衬托其虚伪。小说几位女主角最放飞自我的时刻,则让人想起珍・芳达演的《同妻俱乐部》,笑闹间,人生熙熙攘攘、兵马倥偬都可以是姐妹的下午茶时光。

▲拿铁上桌,成英姝乔角度拍照。她兴趣广泛,从摄影到灵修甚至赛车,自言一直以来都对次文化潮流很有兴趣,「因为次文化潮流是生命力的展现,有最多最新鲜的热情。」(图/镜文学)
死亡在前,你要留下什么?
《再放浪一点》其中一条主线是巩丽莲请爱莫为她量身打造剧本,因为可能命不久矣。生命花火最终,谁都想再亮一回。因此,小说无可免的触碰死亡议题,但读者可能会跟着笑。
现实中,成英姝接连遭遇亲友过世,一开始是养了多年的狗,隔一个月后她父亲过世,两年后她妹妹在她出国时动手术,两个星期后也走了。最近她又送走交往二十年的男友。疫情期间,时不时传来她对岸朋友突如其来失去身边亲人,「生命竟就是如此轻易无声无息灰飞烟灭。」
「现在我已经做好准备随时会走。时时刻刻我都在想,人生说走就走,我留下了什么?每天都在找答案,但找不到。」死亡已被预知,成英姝说那就活在当下吧,「但我发现活在当下不是把握什么,而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这些都不想。我的过去与现在无关,而我的当下也不影响我的未来,因为我连明天有没有都不知道。」
话虽如此,成英姝说死前还是有一定要做的事:删掉计算机里的草稿跟未完成作品。作品不重要了吗?成英姝说,「没了就没了吧。」好像中年以后人生就是不断的救死扶伤,直到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听起来中年后就是一路下坡,但成英姝用喜剧面向死亡,她说写《再放浪一点》写到她自己都会笑。

▲她第一个刺青是十年前刺的。本来不知道刺啥,但有一天想开,就果断去刺了。会不会后悔刺青图案?成英姝说,「会啊,人生就是一定会后悔,但谁在乎呢?人生不就这样吗?想法一定会改变。人生如果没有改变,多可怕?」(图/镜文学)
努力在现世与虚拟获得补偿
《再放浪一点》最浪最好笑的是女人间的唇枪舌战。成英姝爱写对话,尤其是麻利的对话,「我喜欢表达人,要强调一个人的个性,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她的语言。」同时她爱讲话,小学没什么朋友,上课却总是跟坐旁边的同学发表自己的见地,「那人甚至不是我朋友,我只是想说话。」以前跟作家友人动辄在咖啡馆聊七八个小时也不会累。
听起来成英姝很需要热闹,可是她又享受绝对的自由与孤独,想到再谈恋爱,心中会牵绊他人,就让她打退堂鼓,「所以一个人过活就好。」看似潇洒,连作品都不在乎,但成英姝还是有生活之必须——宝可梦。难道不写作时都在抓宝吗?成英姝说,「写作和抓宝并不冲突。事实上,游戏跟人生一样是虚拟的,虚拟的程度没有不同。」
然而,成英姝其实有段时间没玩,重新迷上宝可梦是在她男友丧礼上,遇见二十多年来几乎没联络的男友姐姐。等火化时,成英姝发现他姐姐在抓宝,于是也跟着抓。对方还教她新出的团体战要怎么打。听起来像卡缪《异乡人》里的情节,只是没有人被抓去审判。
女主角爱莫在里头说:「我认为戏剧的诞生,来自一种补偿作用,对现实、真实生活的补偿。」成英姝说写小说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是我可以一直写下去的原因。」所以现世里有很多遗恨吗?要用小说给自己一个交代。就像她手臂上的刺青,也是给自己的交代——当初是为了证明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有你没有才刺的,「现在我发现其实我跟别人本来就不一样啊。」
「不过至少死在哪里时,别人马上就知道是我的尸体。」成英姝摸着手腕上象征灵性的蛇图腾说。也似抚起发痒的伤口。
《再放浪一点》新书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