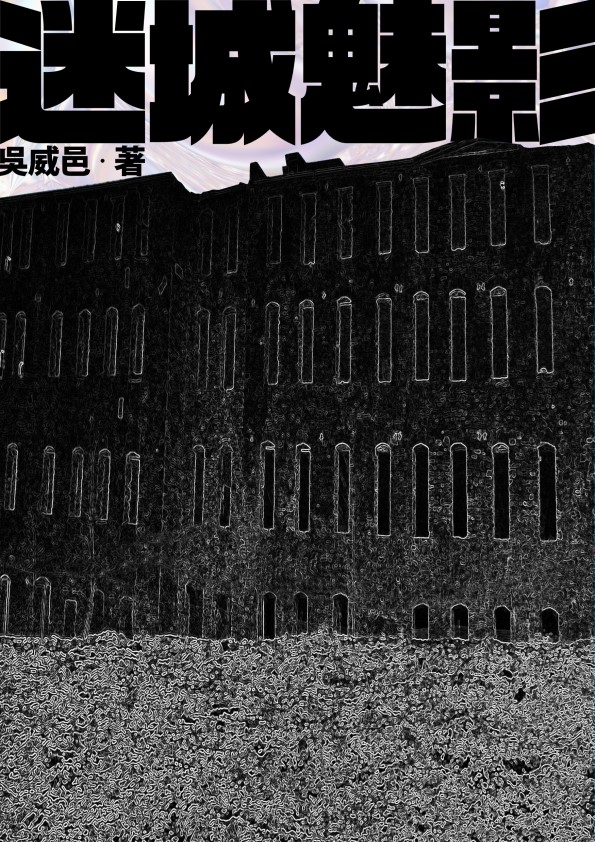【作家特写】书写,是在暗夜中寻找出路 吴威邑:人生就是不断被调包的过程
文|佐渡守
2018-12-10
 立即阅读:《魔王》
立即阅读:《魔王》
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形容对吴威邑的第一印象,应该会是「适合穿白T的大男孩」。然而,反差极大的是,从惊悚小说《一生悬命》、《栖鸟》一路到搓合历史与魔幻的《艾黛尔戴斯》,他笔下的主角却一个个卷入诡谲的黑幕之中。
与之搏斗的,是主角抵抗命运的意志,以及至善的光明面。
故事最后,是光明战胜黑暗,还是随之殒落?吴威邑将他对人性的好奇,投注在小说中那黑到化不开的暗夜与迷巷。
混杂各种类型的老灵魂
访问一开始,我故意问他是几年次的。因为他文笔洗练,作品结构庞杂,描写老成,行文间还有近乎自语的呢喃;像是倒了孟婆汤的老灵魂化为说书人,写小说细诉嘈嘈切切的前生往事。如果不是主角时而耍耍年轻人的幽默,我实在无法想像作者不过是1990年生的大男孩。
「应该是脑袋被调包了。」采访前,我对年轻的吴威邑下了这个很不科学的结论。然而,吴威邑告诉我:「人生本来就是不断被调包的过程。」
调包的过程,得从创作起源讲起。吴威邑的写作起步相当早,高二开始便提笔写作,且一写就是长篇,揉杂历史、魔幻、惊悚、爱情与近代武侠等,交出难以分类的小说风格。
「当时我是住宿生,晚自习时常常偷看小说。记得那夜窗外下著雨,我在看西班牙作家鲁依斯.萨丰的《风之影》。也不知是外面的风吹进来,还是被手上的书给震撼了,看著看著,我突然全身起鸡皮疙瘩。从那之后,就开始写了。」写作念头就这样有如神谕般降临。
 吴威邑书柜里有各种类型小说,一如其创作,混杂不同类型。
吴威邑书柜里有各种类型小说,一如其创作,混杂不同类型。
吴威邑自言「爽写了一两年」,接著上大学。虽然念的是土木,吴威邑却在此遇到创作路上第一位恩人──同校的中文系教授。每当他写完一本小说,送上初稿,就能获得教授写满整页红色眉批的回馈。
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当初以《艾黛尔戴斯》参加小说奖,除了被评审郑秉泓列为「印象最深刻的作品」,第二年郑秉泓还特定将他与当届首奖并陈,专文推荐。
郑秉泓形容《艾黛尔戴斯》营造的画面具备30年代好莱坞黑色电影元素,剧情结合奇幻色彩与台湾历史,是最值得影像化的一部作品,「这个以战后台中为背景的故事,很难用三言两语将情节交代清楚,但有别于过度耽溺某种『自己』的作品,它让我看见了在其他台湾电影中前所未见的世界观──与现实若即若离,充满无比想像。」
也有评审形容吴威邑小说的「时代感很古怪」,其实,这正是他小说特色的一体两面。只要你耐心读下去,就会被字里行间强烈的电影感吸引。《艾黛尔戴斯》便是一部难以分类的作品。
故事发生在民国49年,台湾还在戒严,肃杀之气仍盘据这座夹缝在冷战体制下的小岛。主人翁桂子虎是家境富裕的名作家,在某次宵禁夜晚外出,竟意外寻访地下舞厅「白玫瑰」。在此,他相遇神祕女子露露,之后又获得一把据说可找到日军遗留宝藏的钥匙。在执政当局追杀与死神「艾黛尔」的环绕下,桂子虎一步步找出宝藏所在,同时梳理他牵连中日台敏感关系的身世之谜。
《艾黛尔戴斯》故事层层推演,将戒严之岛描写得有如虚幻的巨大迷宫,读者可能看至全书三分之一处,都在疑惑「艾黛尔」是人还是鬼?或如《一生悬命》,也会让读者怀疑是在看恐怖小说还是纯爱故事?混杂的类型血脉,正是吴威邑的独特之处。人生是不断被调包的过程,书写亦若是。
写不可说的历史让人们重叠在一块
吴威邑的小说还有个特色,再怎么微不足道的配角仍有鲜明的人设譬喻,例如《栖鸟》里的「祝融」像嗜血的秃鹰;掌权一时的冯玉河则是裹著糖衣的蟾蜍──看上去很美,吞下肚要人命;至于《艾黛尔戴斯》里的死神更是让人直觉联想彼岸花曼珠沙华,绽放危崖,勾人心魄。
 「小说会带著读者走,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片刻的感同身受,最后说出『好看』两个字,我就很开心了。」 尽管吴威邑的小说千回百转,有无尽的黑暗,他仍希望读者按图索骥,跟著主角找寻出路。
「小说会带著读者走,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片刻的感同身受,最后说出『好看』两个字,我就很开心了。」 尽管吴威邑的小说千回百转,有无尽的黑暗,他仍希望读者按图索骥,跟著主角找寻出路。
接著,我们谈到作品影视化。当读者受剧中人吸引,脑中就会浮现「最适演员」的影像,我问:「所以《栖鸟》里的『教父』,在你脑海中是刘德华的形象吗?」此时吴威邑仅露出不置可否的笑容,却让我不禁想起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恶鬼出巡般的杀戮,以及主角低回压抑的感情。
凡此种种,到底是怎么从他年轻的脑袋冒出的?由是,我们谈到小说的历史背景。
「我会以戒严时期为背景,正因那是『不可说』的历史,有太多伤痛、太多隐瞒,可是人人手里却都握有它的蛛丝马迹。然而,就连我爷爷都对它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隐晦的历史成为吴威邑搭建魔幻故事的舞台。但台上故事结束,看戏的观众除了娱乐,又从中获得了什么?
「当作品完成,与作品最亲近的就是被小说镜射的读者。其实抽掉国族与政治,看到的也就是人性面与社会的不公不义。那种时间的距离感与世代差异,反而会因『抽离』而与我们重叠,让我们去看见:原来人性或者说历史就是不断的重蹈覆辙。」
写小说是为了不无聊
被问到为何会想创作?吴威邑的回答十分耐人寻味。他说:「你必须想一件值得做一辈子的事,这样才不会无聊。」语气如浮云,说的却是重重的一辈子。
 关于创作,吴威邑说:「你必须想一件值得做一辈子的事,这样才不会无聊。」画画,也是他不无聊的方式。
关于创作,吴威邑说:「你必须想一件值得做一辈子的事,这样才不会无聊。」画画,也是他不无聊的方式。
当写作变成一辈子的事,自然也没有什么时间点可以停下来。重点是前进。
大学毕业后,服完兵役前,已有现成工作等著吴威邑。然而,他一看到电影小说奖开征,就二话不说辞去工作,决定用最后一个月薪水生活,专心写作。
如同《艾黛尔戴斯》里的桂子虎,有自己人生的轻重缓急,吴威邑每天吃千篇一律的白吐司加自制马铃薯沙拉,也丝毫不动摇对写作的追求。他不讳言,写《艾黛尔戴斯》是他的作者生命与作品最紧紧相系的时期,而这件事发生在他人生至今最困顿之时。
「什么都不在乎,又什么都在乎」或许可当作吴威邑与他笔下人物最相近的特质。为了写出他口中所称「文字创作,是作者意念纯度最高的作品」,吴威邑常常写到「脑壳发烫、背脊发凉」。这可不是心理形容,而是真切的用肉身碰撞文字。「因为我都躺著写东西,而且会写到脑袋烧到一定程度才停下来,还因花太多时间维持姿势,脖子与背脊血液循环不好,下场就是僵硬酸痛。」
即使同学笑他卖出一本书,也只买得起一杯豆浆,吴威邑说:「复杂的剧情留在作品里就好,人生简单比较好,像我躲在作品后面,也是安安稳稳的。」
正因如此,他不会锁定读者来创作,而是转换每一滴生命力来完成作品,「读小说不像听一首歌,可以依照悲伤或快乐来挑选歌曲。小说会带著读者走,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片刻的感同身受,最后说出『好看』两个字,我就很开心了。」
尽管他的故事千回百转,小说世界有无尽的黑暗,吴威邑仍希望读者按图索骥,跟著主角找寻出路。读完一本小说,诚然不能解救人生,至少能帮助我们回望自己所在岛屿的来时路,那层层叠叠反反覆覆暗藏吃人历史的曲折迷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