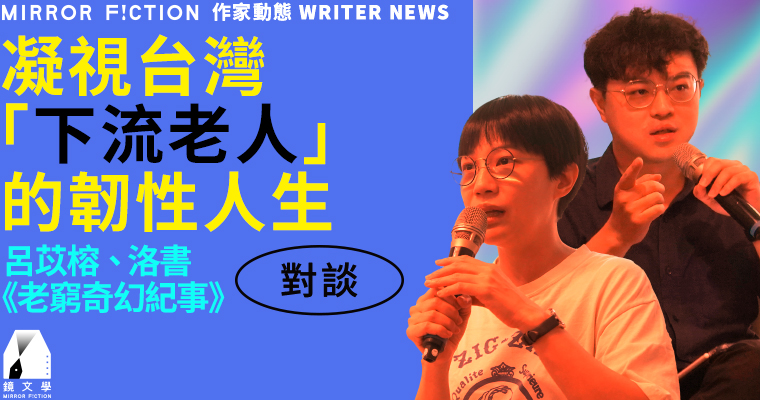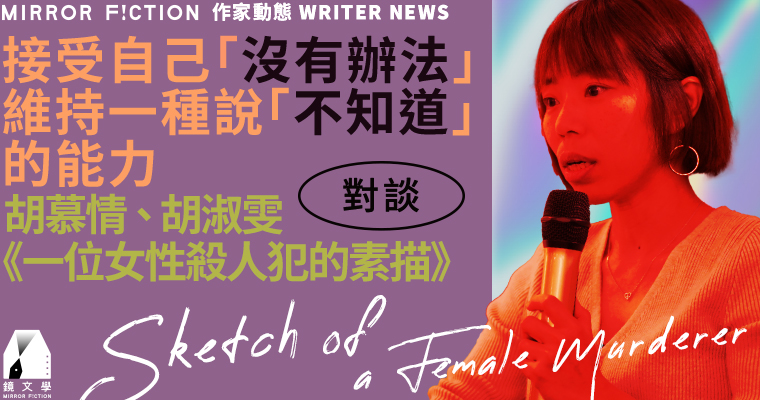宮廟的孩子成為作家——浮果談他的「取經」之路

小說《開著福音車徵廟公》深入描寫臺灣的進香文化,以宮廟二代與牧師二代的男同志伴侶為主角,展開一段尋找廟公的公路之旅。
究竟族群融合能否包含信仰?作者浮果用輕鬆筆法書寫歷史和民俗文化,以乍看衝突的設定處理生命難題及家庭困境,希望藉由小說鬆動固化認知,傳遞宗教與性別實際上是可以流動的概念。
與談人王君宇身為本書的責任編輯,以小說為軸,嘗試挖掘浮果對於寫作、宗教信仰、家庭關係等面向的現實映照,進行一場「靈魂拷問」式的深度對談。
走訪宮廟的孩子成為作家
「我四、五歲就跟著父親走宮廟,坐遊覽車去進香。」家庭背景使然,民俗從小就在浮果的生活佔有一席之地,看過信徒送神轎、乩童訓乩,從疑惑、參與到擁有自己的理解,這些記憶都成了本書的創作養分。
書中的進香之旅途經許多宮廟,描繪了不少神明故事和歷史,這些書寫憑藉的不只是兒時記憶,也來自浮果在臺南嘉義一帶實地走訪的田野調查,除了現場感受信徒拜拜的情況,廟宇牆上或石碑上的文字,往往更是網路難以搜尋到的資料。
期間,也有發現與印象不符的情形──東石的港口宮乍聽之下位於港邊,他因為不放心,特別以家族旅行的名義帶家人去附近玩,才發現實際上離港口有段距離,幸好來得及修正。為了釐清同一位神明的不同解釋和由來,也必須查文獻、看圖鑑,例如有些神明通稱池府王爺,指稱的卻是不同人;又或者許多廟都會強調自己是「開基」或「第一」,就得去確認年代或區域。
改了名字寫進書裡的廟,實則來自他學生時期當廟公的真實經驗。彼時舅公是廟的負責人,某天忽然因為欠債跑路,父親擔心廟的存亡,指派他下課去顧廟。「廟裡不同人來來去去,不確定是信徒還是小偷?有趣的是,這些平常可能不會想接觸的人,反而會因為神明的共同信仰而開啟話題。」
廟裡沒人時,他覺得無聊,就跟神明說話,保佑自己考試一百分云云。這段廟公經歷,讓他開始思考人跟神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形塑出自己對神明的認知。
同志身分 vs 傳統父親,嘗試在衝突中了解對方處境
浮果寫小說喜歡與生活結合,從真實的人身上找靈感。書中,主角的爸爸取材自他的父親,但形象卻完全相反,相同之處在於父子相處。如今與父親是同居關係的他,要和這位室友重新認識與互動──「我爸有屬於自己的生活,不太喜歡管我。他是那種吵架不輕易妥協的人,一定要先拉下臉去求和,幫他找台階下。」
寫小說時,他覺得父親不盡然是不理解兒子,有時只是不願承認──面對其同志身分,傳統背景長大的異性戀男性需要時間去消化,也變成小說角色之間得以發揮的衝突。
他坦言,寫書時嘗試處理父子關係,最後讓爸爸的角色選擇接受也是有其原因。小時候家族聚餐,有人問起家中另一位同志,父親說「他是成年人了,做任何決定都是他的事,我們無權要求他配合我們的期待」,讓浮果覺得父親想法開明。
現在回頭看,父親與家人衝突而生氣時,經常自己先冷靜退一步,過幾天調整好情緒,才會試著讓對方知道他的想法;傳統父親或許是威嚴的存在,但可能也是偽裝,如同書裡的宮廟主人或牧師,嘴上很壞,但還是有面對兒子是同志的方法。
帶著不同的宗教背景,主角男友的爸爸同為單親家庭,也不太能接受兒子出櫃,這兩對父子的關係是如何構想?他說,拋開宗教去看,尋找兩對父子當中的共通性,會發現傳統男性被賦予了許多責任,往往無法輕易表達自身情緒,僅能透過間接方式求和求好。
「對長大的兒子來說,反而必須去教育父親,讓他認識到小孩已經長大,可以試著跟兒子當朋友。」書寫時,希望親子關係的相處不是上對下,而是能在衝突中盡量了解對方處境,「不見得認同或理解,但至少可以去接受,就是很大的突破了。」
神明是心靈信仰,真正的改變仰賴自己
編輯王君宇指出,書裡的宗教觀近似泛靈論,各個宗教的神可能都源自同個地方,只是在不同文化中擁有不同形象,因此好奇他在創作上的宗教觀。浮果分享身邊認識的虔誠基督徒,因為家人手術成功而改信泰國四面佛的故事,讓他意識到宗教即信仰,是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的,有沒有從信仰過程中「滿足需求」,才是更明顯的原因。
如今虔誠如他,反而不覺得自己有事特別需要問神,真正求神明的次數也少之又少,父親在這方面影響頗深:「我爸說神明的存在是信仰,給你心靈支柱,但不可以當成有求必應的對象。為什麼一定要保佑你?你跟其他人都一樣。如果特別去照顧你,那也有失公平。」
有段時間他幫家裡還債,忽然明白求神問卜是心靈信仰,要真正改變事情,還是必須自己努力。當然,努力不見得能改變,好比欠債依然要還,但怎麼還?跟銀行協商、以誠意請人協助,對自己有利的方式要主動爭取。信仰能給人力量,但太過依賴這個力量去做事,卻容易走火入魔。
回推到寫作,浮果自問,成為作家是夢想還是目標?他說,很多時候是必須去做的目標,因為光用想的,就只會是夢而已。
撰文 侯伯彥 ◆ 攝影 鏡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