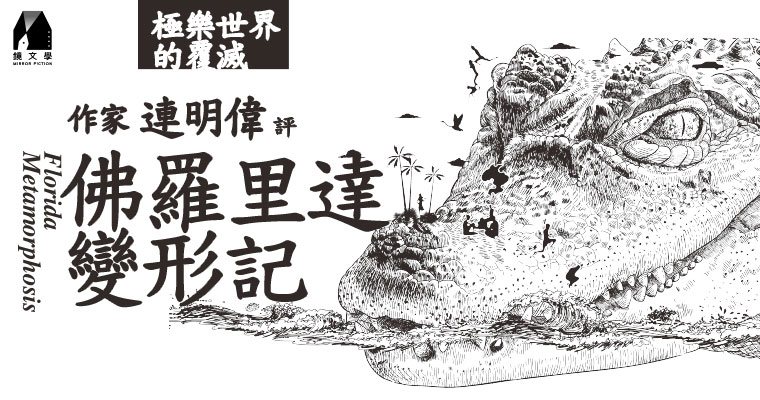
极乐世界的覆灭──连明伟评陈思宏长篇小说《佛罗里达变形记》
当破土迎接第一缕阳光时,它整个形态毫无艺术性可言 植物之子,也如人类之子一样幼苗越长越高,把各个器官组合成整体再反复、再创造可能发育成无穷尽的不同形态。你看:仿佛每片叶都被精心雕琢――锯齿状叶缘,波形缺刻,针状叶片在叶柄支撑下,与整棵植株交织为整体命中注定!歌德《植物变形记》 从《鬼地方》徙至《佛罗里达变形记》,“夏日三部曲”第二部妖异直袭,不容喘息。作家再次凭借招魂本事,探索人之渴求、忏悔与变异。鬼魅随行,附身不再单纯指涉肉身,深入记忆,使活人变成死鬼,使死人变成活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南方不可以止些。“小史”作为长篇小说开篇切入视角,为人名,为古代职掌记谱礼仪职官称谓,为诸家野史,亦指涉文明别传。一心离世者向友人递送邀约,遗书号令,聚拢四散败兵,命运歧路,离散分轨,蚂蚁运尸途径再次浮现,准备重回西方极乐世界,共同拼凑历史面貌。若言,《鬼》书是以逃至未来的异境“他”者,归返原乡,审视“他/他们”之生命故事;《佛》书,则以“他/他们”,重新从原乡抵达异境,还原过去,聚焦另一无所不在的“他”者。两书横跨巨幅时间,然而,最终抵达的地理、精神与意涵,却有所背离;亦即,两本小说内在意义之起始,互为陈述,同时互为抗衡。六位龙子龙女考完联考,参与“莲观基金会”举办的“佛罗里达暑期少年英语游学团”。领队蛋头带领,地域越界,扩增内在空间探向自我,一一凝视各自家庭境况。小说主要调动两个时间与两个地理位置。时间切片,是1991年的越界之行与2020年的瘟疫之年;地理切片,是佛罗里达与台湾。时空广袤,相互牵引,从中演绎人心诸多变化。龙子龙女各有境遇,因个性、潜能与家庭而走向不同方位,然而探讨不仅于此,私我演变除了情感需求,除了个人意志,隐然透露条条路径抉择,早有历史幽灵惘惘纠缠。表面,近三十年转变,揭橥肉体解放、感情冲动与思想桎梏,深入其中,则得研析整体脉络对人的影响。故事除了聚焦青少启蒙,肉体花草,精神蜕变,更是指向蒙蔽未知如遭操控的背景。位置从亚热带台湾前进热带佛罗里达,再抵至西方乐园避难碉堡,居此,文明洋葱剥落,解除限制,泯灭界线,紫夜、百香果、短吻鳄、火山蚁丘、犀牛、壁虎、绿鬣蜥、猫、红鹤、螃蟹、猫、红树林、蟒蛇等随侍在旁,莲座化为红树林,龙子龙女化为蜥蜴,并非异化为另一个我,而是在另一种文明可能性中重新雕塑,乃至发现原初自我。感官掌控,声色犬马肆意解放,展现兽性通感,深刻唤醒五感。视觉:凯文之精准素描。嗅觉:克莉丝丁之敏锐嗅闻。味觉:安妮之食蚁欲望。听觉:阿曼达之琴奏,莱恩对音乐专辑之迷恋。触觉:莱恩、克莉丝丁遭遇的肉体伤害,角色展开的情欲探索。饮酒,嗑药,著迷新颖食膳,性向暧昧游移,肉体解放跨至精神,乃至最后,无意间唤醒噬人之欲。罪恶迷人,同时迷惑于人。跨入现代文明,人的原初之欲毕竟有其底线,一旦跨越必定深刻烙印,无可复返。经由他者唤醒记忆,原罪胎记,将一辈子囚困探索者。有心无心,均为罪过。乐园揭晓,并非温驯可亲的动物园,而是深藏危机的热带兽园。以愉悦为出发的狩猎,沦为相对意义的野蛮,除非继续留存地下碉堡,展开另一文明向度。龙子龙女偶然造成“黄祸”(Yellow Peril),逃离乐园,返回东方,受限早已建构之道德方寸,终生愧疚。遗留者或自尽,或精神崩溃,西方文明亦无法容许此种流于冲动未被认可的杀戮。乐园沾血,自此衰落,地下碉堡正式敲钉封棺。西方避难乐园并非单独存在,紧密呼应东方“莲社/垂莲小佛堂”。亚裔意象错综贯穿小说,并与西方符码有效抗衡,Yellow、龙的传人、莲花、香港餐厅、指月割耳的传说等。细探机构成立缘由,早已背离佛教教义,自成体系,独立运作。从党国体制的地下组织避难所,转化为优生学、分级人类、高等低等之“塑人”机制,再转型为慈善助人基金会,龙子龙女在此架构诞生,即使亟欲远离,却难逃掌控。西方避难碉堡的乐园建造者为孤狼杰克,东方躲避党政的地下组织创办人为双性人,东西极乐世界的领导者,均是各个文明制度摧残下的“畸形者”。由于受创,必得活在自主运作的场域,唯有坚壁清野,才得以生存。肉体之自慰,精神之自卫,凭借不受认同的畸形,勃生另一文明向度,宽容鳏寡孤独,接纳老弱伤残,瓦解单一文明故事法则。只是,空间护卫,未能演化另一规模的章程、训诫与道德,紧接势必步入衰败。角色的肉体探索、情感抵牾与精神转变,在畸形文明的互惠之下,萌发规范之外的火种。所谓“变形”,非指终点,而是探向本我之历程,一路巾帼罗襦,搽脂抹粉,天女散花,狂飙文字声色感官,展演行为浮光浪蕊,虚构中隐匿虚构,直至所有秘密一一接露,最终,得以知晓,作为“人”,其实无法避免残暴――于是纵情,于是性欲,于是乱伦。人之原始特征被激发,喷勃飞溅,一方面破除禁锢,另一方面探索文明框架,乃至人在社会系统底下的失误、乱码与突破意志。预设的教化模组之中,原始的欲望、人的养成与道德的培养,均成为诅咒。进而,探向内在意义,无意有意的杀戮,不再只是罪过,不再只是一辈子的忏悔,不再只是某种必须隐蔽的邪恶,巧妙转化,成为无法承担的抗辩,认清自我,借此正式背离东方西方极乐世界。堕入畸形的历程,同时揭露,远离畸形的路径,东西文明野蛮高贵在此正式崩解。作家的野心不可小觑。结合公路浪游、青春启蒙、性别认同、感官探索、忏悔告白、造人工程等主题,演绎出文化冲突、人类意志乃至文明起源雏型等。然而,或可斟酌,异境对语言造成的切割、镕铸与背离;同时,当故事不断解构本为虚构之体的小说,任何摧毁,无限翻转,易将轻易丧失意义厚度。兹因种种明显特征,仿佛刻意背离写实小说,通向寓言,指涉神话,展开更为交错、虚实与庞杂之象征辨证。乌托邦,无何有乡,意欲建立必得先行摧毁,诚心祭献人命;然而,献上人命,并不保证乐园必定到来,先行抵达的总是幽灵。鬼之言,佛之语,莲花瓣瓣垂怜,命运终将揭露我们本无堕落倾向之原初。本文作者连明伟一九八三年生,暨南大学中文系、东华大学创英所毕业。曾任职菲律宾尚爱中学华文教师,加拿大班夫费尔蒙特城堡饭店员工,圣露西亚青年体育部桌球教练。现为北艺大讲师。著有《番茄街游击战》、《青蚨子》、《蓝莓夜的告白》等。
+ More